一個干過翻譯的過來人告訴你:為什麼有這麼多爛譯著?
原標題:一個干過翻譯的過來人告訴你:為什麼有這麼多爛譯著?

本來最佳的譯者應該從學者中衍生出來,但現在的機制卻是學者不願干,結果試圖將一些底子不厚的學生直接培養成譯者。最終,整個行業永遠停滯不前,永遠毀讀者不倦。
撰文 | 陶力行
經常會看到有人在朋友圈貼某譯著,然後開罵譯者垃圾。大量爛譯著充斥閱讀市場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如果英文版便宜,我是絕不會冒險買中文版。
我曾干過翻譯的活,誠實地說,是翻爛過幾部作品。干這活以前,我也經常罵這個人那個人是廢物,直到幹了這活以後,我才發現自己也跟廢物差不多。
不敢奢望那些花了錢的讀者對我抱有半點原諒之心,但我還是想解一下這吃力不討好的活到底是怎麼回事。我主要翻譯的是歷史社科類的書籍,所以我在這裡主要談這個領域。
翻譯差,比較流行的解釋當然是翻譯錢太少,以至於無法吸引有志之士投身其中。
但錢這個東西屬於整個鏈條最末端,只是一部分原因,不足以解釋整體情況。事實上,也有很多人並不是為了錢而踏上翻譯這條不歸路的。

圖書行業一年出版圖書近50萬種,即便譯著只作八分之一算,也有六萬種,假設一個人一年能翻兩本二十萬字的書,至少也要三萬人。
中國人口雖然多,但還真不見得有足夠適配的人能頂上這活。如果本身沒那麼多人能勝任,同時又要出產這麼多譯作,最終只能讓不適配的人參與。就這點來說,即便翻譯費上調五倍十倍,也不見得能解決翻譯爛的問題。
當然,我們可以期待改變激勵機制,從而使更多的人投入到長期的奮鬥,直到最終改變。但是對比一下其他行業就可知道,投資回報率高的預期並不必然帶來產品質量的上升——至少在我們這裡不是這麼回事。
翻譯爛絕非個別現象,而是當下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涉及的原因比較複雜,不僅有行業機制的問題,還有歷史遺留的問題。
好譯作標準很簡單,即能夠準確、清晰、簡潔地反映原作所要表達的內容。
一個好的譯者不僅能將原作者所表述的內容準確地傳達出來,還要儘可能地降低讀者的認知門檻,即幫助讀者以最親近的方式獲取原作品的信息。但是,有時候並不能同時滿足這些要求,當衝突發生時,取捨就變得尤為重要。

▲翻譯家傅雷
翻譯工作里,最理想的也是最難做到的,就是語詞的一一對應。
如果翻譯的是理工類作品或者商務性文件,那任務還算輕鬆。雖然所涉及的語言很專業化,但恰恰也是因為高度標準化、程式化,譯者很容易找到一一對應的語詞。
但翻譯的對象若屬文史哲領域的話,譯者除了要熟悉外文和母語外,還要熟悉兩種語言所代表的文化以及文本的語境,因為每一個語詞的形成都受歷史或社會經驗的影響,在西方某個時間點形成的一個概念,在東方未必就能找得出相對應的詞。
雖然字典能夠給我們提供一些幫助,但字典編撰的主要方式還是對過去互譯經驗的歸納,它並不能窮盡一切可能性。相對來說,有共同經驗的語詞更容易互譯,比如hungry——餓了,sugary——甜的。
若要翻譯沒有共同經驗的語詞就要通過類似於拆文解字的方式,首先將這些語詞化約成有共同經驗的基本單元,然後再將基本單元重新組合成新詞,像我們使用的哲學——philosophy、經濟——economy之類的詞語,當初都是日本人通過這樣的方式給譯出來的。

這裡可以提一下,日本思想界和中國思想界差不多是在同一時期開始啟動西學翻譯,但兩者態度很不一樣,效果也很不一樣。
日本思想界力主把準確性放在第一位,因為在他們看來,學習外人知識是第一位,而學習的起點就是準確地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而中國思想界沒有這麼看重準確性,受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影響,像很早就提出「信、達、雅」標準的嚴復也把達放置於信之前,即流暢性優先於準確性,後來的魯迅倒是把準確性放在第一位。
為了解決語詞不通譯的問題,日本思想界從明治維新時代以來,就開始大量啟動了語言的清晰化工作,把傳統語言分析化、語詞原子化,這為後來的翻譯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另外一種做法就是保留原詞,只是採取音譯的方式,然後將這些外來詞內化成自己的語言。這樣做,表面看起來很僵硬,但好處顯而易見:
一來是避免不同譯者因為不同的理解而造成的歧義;二來是容易在知識界內部達成共識,形成行業標準,因為越是去個人性,越是能實現標準化;第三,就是豐富了自己的語言。

專註於準確性的做法符合日本人的行事風格,大大降低了後人修改的風險。我們沒有把這一標準作為底線共識,經常把「約定錯成」當成了「約定俗成」,以至於鬧了不少麻煩。
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constitutional monarchy這個詞,即英國的「立憲君主制」,中文把它翻譯成「君主立憲制」。十多年前,學術界就有人主張糾正,但過了十多年,錯誤還是糾正不過來。
同樣一個詞,在古代是一個意思,在現代是另一個意思,雖然英文中用同一個詞指稱,但是翻譯的時候該不該用同一個詞對應,又會變得很有爭議。我之前在翻譯一部政治學作品時就遇到過類似的問題。
在這部著作里,Patrotism是一個現代詞,十八世紀才有人用。查字典,你可以知道它的意思是「愛國主義」,但是作者從心理學上追溯這個概念的起源,認為古風時代就有這種觀念意識,比如英雄赫克托耳對其城邦特洛伊的情感認同。
對於譯者來說,這裡的困難是,在古風時代,根本還沒有出現國家這類東西,如果用「愛國主義」一詞,顯然是錯的。
我們現在說的「國家」實際上指的是,自十八十九世紀開始出現,由民族發共同體發展而來的有主權意味的政治實體。古希臘沒有這個東西,所以我只能翻譯成「懷邦主義」「家園主義」之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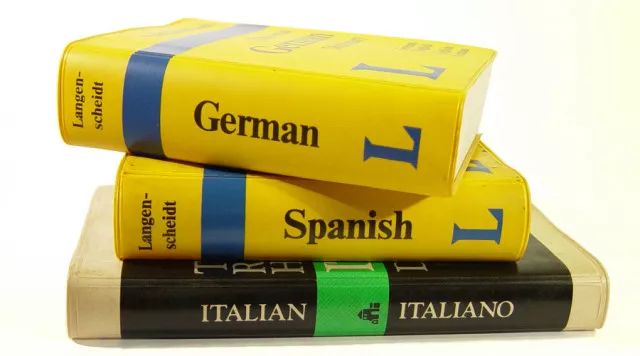
在翻譯的時候,若用兩個不同的詞指稱,就會割裂兩者的聯繫性,但如果用同一個詞,就會讓讀者產生混淆。所以我在處理的時候,就採用譯者聲明的方式解釋。
說這些是想指出,翻譯是一個高度專業化的工作,需要有超越於語言本身的知識基礎作後盾。但現實卻是,當下譯者普遍缺乏這樣的知識基礎——這和我們翻譯市場的運作機制有關。
我們買書的時候,經常會看到「××系列叢書」這樣的分類標註。這類書籍要麼是出版社立項找學者組團隊翻譯,要麼就是高校學者組團隊立項然後聯合出版社推進。
雖然都有專業學者介入,但翻譯的主體並非學者,而是學者門下的研究生。一來是因為翻譯不算學者業績,不算科研成果,所以學者懶得干;二來則是因為翻譯被當做了培養研究生的主要手段。
因為沒有掌握到研究範式,所以國內大部分學者做學術的方式就是追國外熱點,翻譯國外前沿作品。帶學生的方式,也就是先指導學生翻譯,然後再讓學生做有關這些前沿文獻的研究性論文。
但國內研究生的前置知識嚴重不足,語言技能也很匱乏,應對不了翻譯的任務。相比於國外,國內文史哲社科類學生在本科階段的學習都很弱。

▲相比於國內,西方社科類學生在本科階段的學習強度更大
在美國,普通大學高年級本科生每學期每門課就要閱讀二三十篇高強度文獻,一門課至少完成兩篇寫作。但是國內一門課一般也就讀一兩本書,達不到高密度高質量的信息獲取,知識的成長十分有限。
另外,美國課堂是以論證(argument)為主,中國課堂是以介紹為主,學習範式差異使得我們在讀人家作品的時候會形成嚴重的隔閡。語言方面,研究生的普遍水平只夠剛過六級,對於翻譯來說,這相當於赤裸上陣。
本來最佳的譯者應該從學者中衍生出來,但現在的機制卻是學者不願干,結果試圖將一些底子不厚的學生直接培養成譯者。這裡的問題顯然會很多,比如學生畢業之後,如果不進入學術圈,翻譯的工作幾乎不會再從。
說輕的,就是資源浪費,每次都要讓一波新手出來把譯書當作實驗,實驗做砸了,書也毀一波;說重的,就是翻譯經驗永遠無法累積,無法形成系統性的知識和推進工業化。結果就是,整個行業永遠停滯不前,永遠毀讀者不倦。
日本人就不一樣,翻譯的作品也被算作學者的業績,這樣就能促使專家從事翻譯工作。

▲日本明治維新時代,提倡學習西方社會文化及習慣,翻譯西方著作
事實上,自明治維新時代以來,翻譯就被日本政府放在知識戰略的高度上,因為它能幫助日本人了解世界。獲取知識,就是為了實現了解。
在我們這裡,一味追求發論文,出成果,但卻忘記了學術的首要目的是促進知識,推進理解,而不是發論文。
在這點上,日本人想得明白,放在知識推進的高度,翻譯和發論文都只是形式而已。我們至今尚未理解這一點,最後的結果就是為了發論文而發論文,為了翻譯而翻譯,反正兩邊都沒做好。
而且日本有良好的閱讀市場,所以翻譯可以獲得很高的報酬,這也推動了翻譯市場的繁榮。
有意思的是,日本雖然民間外語不好,很多高校的學者外語也不好,但是他們的知識界一點不封閉,他們對於世界前沿的了解一點不滯後,顯然這應該歸功於成熟的翻譯市場。
總的來說,買譯著,買到好的是運氣,買到不好的是命運。我只希望自個兒有點錢,能把標註自己名字的譯著通通買下,不要等多年以後還被人拿出來指摘一番才好啊。


※誰沒有作過弊?但只有《天才槍手》代言了我們
※「天貓雙11」不只是網購,「五新」秀出中國軟實力人魚線
TAG:冰川思想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