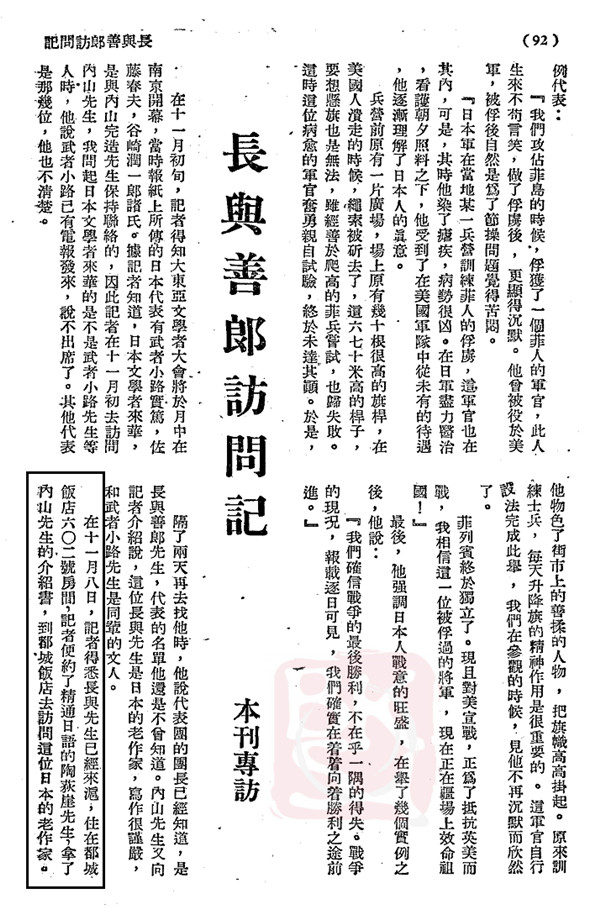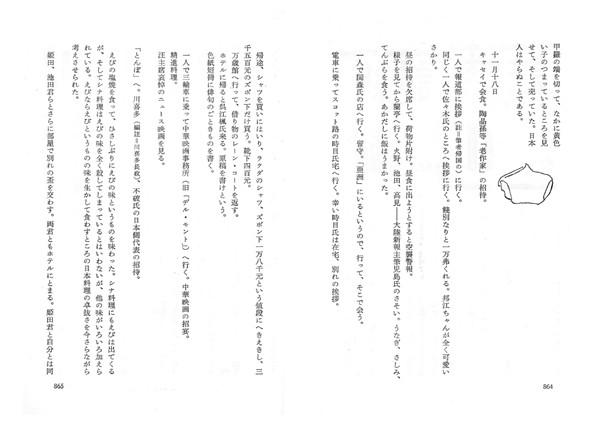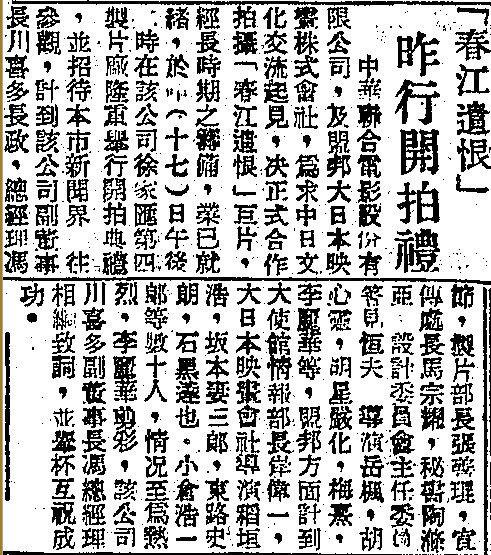祝淳翔:上海淪陷期的日語翻譯陶荻崖
原標題:祝淳翔:上海淪陷期的日語翻譯陶荻崖
近幾年一直忙於整理《陶亢德文存》。編務臨近尾聲時,有友人忽然問我知不知道「荻崖」,說是有人認為這也是陶亢德的筆名(詳見塗曉華《上海淪陷時期〈女聲〉雜誌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76至179頁)。這一提法聞所未聞,剛想發聲埋怨,友人緊接著說,他覺得荻崖不是陶亢德,故遲遲未提,以免徒亂心神。現在我終於有了餘暇,重新檢視一番,確證友人的觀點不誤,而且還真的有所發現。
先看塗曉華在書中如何介紹:
荻崖,即陶荻崖,是淪陷時期最重要最活躍的日本文學翻譯者。他活躍在《雜誌》《風雨談》《女聲》《文友》等雜誌的《日本文學介紹》欄目中。筆者在所接觸到的多本介紹淪陷區上海文學的著作中,沒有看到談荻崖的文字。通過閱讀《雜誌》《風雨談》《女聲》雜誌,結合陶亢德的經歷,在比較、印證之後,筆者以為荻崖即陶亢德,儘管各種版本的陶亢德小傳中沒有筆名荻崖出現。
荻崖姓陶,但非陶亢德
荻崖可冠以陶姓,至少四見:
一、1943年2月15日《申報》第2版報道《市府宣傳部昨召開文化界談話會》,稱前一日上午十時,假江西路都城飯店二樓,舉行文化界談話會,市長陳公博、宣傳部長林柏生主持會議,並列出參會的七十餘名文化人中的55人名單。此名單不依姓名音序或筆順,其中陶荻崖排名第48,列於「左俊生」之後。
|
1943年2月15日《申報》第2版報道
二、1944年1/2月合刊《風雨談》第9期目錄中顯示陶荻崖翻譯泊萊姆·羌達(今通譯普列姆昌德)著的《咒語》,雖則正文僅署荻崖。值得注意的是,本期雜誌還刊出了陶晶孫《創造三年》以及陶亢德《自傳之一章》。
三、1944年11月號《雜誌》第14卷第2期「文化報道」預告稱:「陶荻崖譯之橫光利一名著《後[紋]章》,都二十萬言,將於年內由東方文化編譯館出版。」同一頁上還有:「陶亢德有志寫一二十萬言之長篇《亂世男女》,以上海香港等地為背景,將有不少作家在該書中露臉。」又,荻崖在書評文章《橫光利一的〈紋章〉》(《讀書雜誌》1945年第1卷第3期)的開頭,談及此事原委:「去年秋末,受到東方文化編譯館小竹和武田兩先生的囑咐,就決定開始翻譯日本橫光利一氏的名著《紋章》。……三個月之間,總算把十七萬餘字的初稿譯成了。……現在除了等候作者的譯序之外,還在校改之中。」可知譯稿確已完成,只是最終我們沒有見到成書。至於陶亢德的小說,估計從未動筆。
四、1944年12月號《雜誌》第14卷第3期以「文學者印象」特輯形式,大幅報道了前不久在南京舉辦的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特輯前言」稱:日本代表來滬時,本社曾約諸代表聚談,並特約陶荻崖先生記錄成文,曰「日本文學者剪影」。內頁中有記者專訪日本代表團團長的《長與善郎訪問記》,稱「在十一月八日,記者得悉長與先生已經來滬,住在都城飯店六〇二號房間,記者便約了精通日語的陶荻崖先生,拿了內山先生的介紹信,到都城飯店去訪問這位日本的老作家。」荻崖《日本作家剪影》則寫大會結束後,與會的日本作家一行返滬,作者跟隨《雜誌》社的吳江楓,邀請日方代表長與善郎、豐島與志雄、阿部知二、高見順、火野葦平、河上徹太郎、小林秀雄、草野心平及池田克己等人去四馬路「呷酒持螯」。在路上,豐島對荻崖說:「喂,陶君這兒不是有一家很好吃的蟹粉店嗎?去年一起來過的?」
——之所以不憚其煩地抄錄上述文字,是想把荻崖姓陶這一點確定下來。因為塗女士正是在此基礎上進行推論,進而作出「荻崖即陶亢德」的錯誤判斷的。塗女士擺出論據:首先,1943年8月15日出刊的《文友》第1卷7期編輯室:「荻崖先生精通日文,譯述和創作都很豐富,想也早為讀者所知了。」所以,荻崖是當時文壇的知名作家。其次,1944年12月1日[陶]晶孫在《文友》發表譯文《值得介紹的日本文學》談及,「而現在又接到以前請荻崖先生所做的對於一般中國讀書人需要的日本文學翻譯介紹,抄在下面……」言下之意是,既然陶晶孫文中出現了荻崖,則荻崖不是陶晶孫。此外,塗女士還舉陶亢德譯長谷川如是閑的名著即將刊發,又在1943年8月至1944年3月間(祝按:準確地說,是到2月底)在日本呆了半年,從事「日本文學翻譯」工作,故認定荻崖即陶亢德。
|
豐島與志雄
|
1944年12月號《雜誌》第14卷第3期
可惜,這純是誤會一場。經查檢,1941年至43年間,荻崖在《經綸月刊》《日本評論》等刊物上發表過不少日本當代小說譯作,即至少在那時,他的日語造詣應該相當高了。但陶亢德那時是否精通日文呢?答案是否定的。試舉二例:
1943年11月出版的《風雨談》第7期,有一篇陶亢德的《東京通訊》,寫他某日去鷺宮訪實藤惠秀,與之用中文對談,並道:「在實藤先生家裡,還決定了兩件事,其一是請他開一張關於日本文化名著的書目,其二是請他在早稻田日本學生中找二位教我日語的教師,這一件事今天有在早稻田肄業的留日學生易君見告,說已請定了一位姓安藤的早稻田十六年畢業生,大概下周起我要天天あいうえお了,但不知這個老學生尚可教否。」
1944 年 1 月 10 日出版的《天地》第 4 期亢德《東籬寄語》,記他在銀座三越百貨公司書籍部買書,發現缺頁,第二天攜書去換,因言語不通,差點鬧出誤會。文中感嘆:「你想言語不通夠多窘人,要是我日語如流,一開頭就說明如此如此,不是省事多多麼?」可見陶亢德當時對日語遠非精通,會話能力尤其弱。
行文至此,還應提一下太原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的呂慧君副教授,她曾於2013、14年在日本學術刊物上發表過兩篇日語論文[佔領期上海における『上海文學』と『雑誌』: 內山完造と中國文化人荻崖、陶亢德に著眼して(戦間期東アジアの日本語文學)--(メディア表象: 雑誌?出版?映畫),《アジア遊學》(167),32-44,2013年8月、橫光利一の『紋章』の翻訳とそれに関わる中國文化人荻崖,《橫光利一研究》(12),117-124,2014年3月],駁斥了荻崖是陶亢德的可能性。但文章我無緣寓目,不知其具體論據為何。
荻崖可能是陶晶孫嗎?
之前我注意到《值得介紹的日本文學》里提及荻崖的那段話,實來自文後附言。假如這是編者所擬,還真不能排除他一定不是陶晶孫。何況還有不少「證據」,例如荻崖參與《女聲》雜誌,而陶晶孫恰是《女聲》的特邀作者;荻崖與內山完造很熟,一起做過訪談,而陶晶孫與內山也是老朋友。前文提及,1944年陶荻崖與豐島是再度見面,彼此熟絡得很。而1943年11月19日《申報》報道「中日文協昨歡宴日本文學家,豐島與阿部兩氏均出席」,其中豐島即豐島與志雄,而作為中日文協的重要成員,陶晶孫是歡迎晚宴的主賓。1944年11月,陶晶孫赴南京參與了文學者大會,而荻崖則在日方代表出發前以翻譯身份去採訪,又在他們回來後與之聚宴。
當然了,反例也有。如前述《文友》1卷7期「編輯室」在介紹完荻崖後,緊接著還有如下文字:「下一期,本刊將有陶晶孫先生等的隨筆,請注意。」下期《文友》里,陶晶孫的稿子如期登場,竟赫然排在頭一篇。——荻崖未曾有過這待遇。
此外,荻崖的隨筆《「你吃過飯了沒有?」》(《文友》1943年第1卷第7期),謂「咱們薪水階級而家無黃臉婆……的獨身傢伙」,假如是自況,則只此一例便可判明他既非陶亢德,又非陶晶孫。因為陶亢德在1942年12月出版的《大眾》雜誌有一篇散文《兒女》,開門見山說:「鄙人年未不惑,卻已是四個孩子的父親。」而據《陶晶孫年譜》,他早在1924年即與日本女子佐藤操結婚,此時也已有了三名男孩。
問題是,上述或正或反試圖將荻崖與陶晶孫聯繫的證據只停留於紙面,不見得都是事實。極而言之,假如荻崖欲「隱藏」真實身份,他文章里所寫的,難保不是為了掩飾而故意「創造」出另一人格來欺瞞讀者的。而雜誌編者也未必知情。這與前述證明荻崖非陶亢德有所不同,因為精通翻譯與否,是客觀事實,是很難掩飾的。種種跡象表明,在1943年至44年荻崖的活躍期,他與陶晶孫之間的時空距離非常近。究竟是不是同一人呢?
陶滌亞現身
1944年11月荻崖與吳江楓接待的日本作家裡有一位高見順,此人平素有寫日記的習慣,1964至66年,東京勁草書房出版過一套《高見順日記》。我於是向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山口早苗女士求助,承她幫忙,當天便掃描兩頁日記傳給我。日記里寫,11月17日夜,雜誌社吳江楓請吃蟹,同行的日方人員若干,偏偏沒提陶翻譯。(有趣的是,此人對大閘蟹的興趣頗大,日記里不僅大談如何拆蟹,甚至附有手繪圖。)18日則記著:キャセィ(即Cathay,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北樓)聚餐,陶晶孫等「老作家」招待。荻崖若真是陶晶孫,高見順何至於一字不提呢?我不禁懷疑,荻崖的身份並不尊貴,極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日語翻譯,所以才會被忽視。假如這判斷靠譜,恐怕更難辦。想當初,翻譯人才著實不少,陶亢德就挖掘過一位譯界能手「越裔」,曾將林語堂的《瞬息京華》《生活的藝術》譯成中文,可至今連其真名實姓都無法搞清,遑論其他。
|
高見順日記862-863頁
|
高見順日記864-865頁
不如換個思路,《文友》是中日文化協會上海分會所辦,既然荻崖是此刊的常客,他很可能是文協成員。由此入手,興許會有新發現。
中日文協上海分會成立於1941年1月29日,至1943年10月4日改組。21日《申報》報道「中日文協昨開文藝座談會」:昨日下午三時,在圓明園路該會,邀請本市著名文藝作家陶晶孫、周越然、楊光政、沈鳳、譚惟翰、潘予且、吳易生、關露、丘石木、魯風、江洪、林微音、楊之華、康民、雷振源、穆穆等三十餘人,召開文藝界座談會,討論主題為「如何介紹日本最新文學作品」。此事,在《風雨談》第7期「文壇消息」中也有報道,名單里則多出一個人名陶滌亞,讓筆者眼前一亮:荻崖與滌亞同音,會不會是同一人?很快又發現,與荻崖一樣,陶滌亞也在《新影壇》雜誌上現身,同樣從事翻譯工作。看來有戲。
此外,《文化漢奸罪惡史》里的一節「和平文化」的「大本營」稱:「在罪積上最大的,還有陳彬龢與日本政府合唱的東方文化編譯館,這一集團,由吉田東祜[祐]等輩主持其間,替東方文化編譯館翻譯的是陶荻崖、左丘、未明等人。」
近復得另一友人襄助,從《民國時期出版史料彙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第十冊中覓得「民國三十三年十月東方文化編譯館事業概況」(奇怪的是,此部分內容與目錄完全不符),中略謂:「本館之設立,原為中日文化協會之企劃」,適申報社長陳彬龢欲以編譯出版日本近代優秀圖書為目的,設日本文化研究所;同時東亞同文書院教授小竹文夫也想以同樣趣旨編譯,經文協當事者與兩氏懇談後,「共表贊同之意」,遂於6月1日成立東方文化編譯館,由陳氏與小竹分任正副館長。此「概況」之「六、附錄」項下之(一)役員及職員名單中,陶晶孫名列「理事」,武田泰淳為編譯主任,而(三)編譯者名單中則出現了陶滌亞,確證荻崖正是陶滌亞的筆名。
彼陶滌亞非此陶滌亞
同一時期,國民黨CC系也有一個同名的政論家陶滌亞(1912—1999)。據《陶滌亞先生事略》(台灣《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二十輯》)記載,此人中學期間即秘密加入國民黨。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以陶憂亞筆名撰文反帝反軍閥。10月,武漢光復,被保送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第六期步科,改名滌亞。從軍之餘,不忘寫作,曾在《革命軍日報》連載《從軍雜記》,被林語堂譽為可與同期女生隊同學謝冰瑩之《女兵日記》媲美。以後又主編武漢《民國日報》文藝周刊《人間》、小報《碰報》,其創作興趣逐步從文藝轉向政論。
他在1939至44年的經歷是:
民國二十八年武漢會戰後,國軍轉進,國民政府遷往陪都重慶,陶公攜眷入川,由中國國民黨宣傳部聘為編撰委員會委員,併兼中國文化服務社服務部主任。蔣公「文膽」陳布雷愛其才,曾欲邀入侍從室第二處工作,遭陶公婉拒;陳乃向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推薦重用,聘陶公為設計委員會專任委員,兼第一組召集人。民國三十一年五月,黃少谷調任第三廳廳長,力邀陶公出任第一科少將科長,主管文宣工作之指導,其後又兼管第四科軍中新聞工作,包括軍報社論委員會,每日拍發各戰區陣中日報,集各軍、師作戰之重要新聞、電訊與社論,日以繼夜、責任繁重,雖在敵機瘋狂轟炸下,從未間斷。黃少谷接任重慶掃蕩報社長後,敦聘陶公為兼任主筆,當時該報社論與戰訊,備受各界重視和好評。民國三十三年,陶公升任第三廳副廳長,兼軍中文化工作研究班駐班副主任。
——上述履歷,足以排除其在上海淪陷期間向滬上日偽系統刊物投稿或現身的可能性。
上海的陶滌亞
隨著檢索方向的調整,上海陶滌亞的身影逐漸浮出水面。
1940年李香蘭主演的電影《支那之夜》由日本東寶映畫公司與中華電影聯合有限公司(簡稱「華影」)聯合出品。1943年5月下旬,插曲《蘇州夜曲》在百代公司灌錄中文版,勝利唱片公司發行,由白虹演唱。(梅珠《白虹灌唱蘇州夜曲》,《新聞報》1943年5月25日)這首歌剛問世便風靡一時,並傳唱至今。此曲的中文歌詞為滌亞所譯:
投君懷抱里,無限纏綿意,船歌似春夢,流鶯婉轉啼。水鄉蘇州,花落春去,惜相思,長堤細柳依依。
似花逐水流,流水長悠悠,明日飄何處,問君還知否?倒映雙影,半喜半羞,願與卿,熱情永存長留。
倘若將時代背景全數抹去,這歌詞韻腳周正,倒是恰如其分地傳遞出蘇州水鄉那柔情似水,情意綿綿的氣氛來。只是不合時宜。難怪當年在唱片上讀到這歌詞的人,會態度鮮明地指出:「大概是敵人在槍刺下壓榨出來的呻吟而強言強歡的"中國人的藝術"吧。」因為「歌詞下卻又分明地有著怪刺眼的字,說是日本什麼東亞軍報導部許可,華北藝術協會推薦的」。(袁微子《心的貞操》,《東南日報·筆壘》1947年2月17日)與此同時,也不妨揣度一下作者的心態,假如歌詞水平低劣,又何必抄錄呢?——譯者滌亞,應是陶滌亞。
又,1944年3月18日《申報》報道「《春江遺恨》昨行開拍禮」:
中華聯合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及盟邦大日本映畫株式會社,為求中日文化交流起見,決正式合作拍攝《春江遺恨》巨片,經長時期之籌備,業已就緒,於昨(十七)日午後二時在該公司徐家匯第四製片廠隆重舉行開拍典禮,並招待本市新聞界前往參觀,計到該公司副董事長川喜多長政,總經理馮節,製片部長張善琨,宣傳處長馬宗耀,秘書陶滌亞,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筈見恆夫,導演岳楓,胡心靈,明星嚴化,梅熹,李麗華等,盟邦方面計到大使館情報部長岸偉一,大日本映畫會社導演稻垣浩,坂本[阪東]妻三郎,東路史朗,石黑達也,小倉浩一郎等數十人,情況至為熱烈,李麗華剪綵,該公司川喜多副董事長馮總經理相繼致詞,並舉杯互祝成功。
|
1944年3月18日《申報》報道
《春江遺恨》(日文名:狼火は上海に揚る,意為上海的烽火)是有史以來第一部中日合拍電影,由「華影」與大日本映畫製作株式會社聯手完成。1944年11月在滬公映。當月10日出版的《華北映畫》第68期公布的名單顯示,影片的中譯亦為陶滌亞。(轉引自邵迎建《電影〈春江遺恨〉幕前幕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1期)
綜合以上所有相關材料,大致能推斷:這位陶滌亞(荻崖)未婚,年紀不大,日語流利,很可能有過留日經歷。任職「華影」秘書期間,參與了至少兩部影片或電影歌曲的中譯工作。同時,他還在「華影」機關刊物《新影壇》上譯介與之有著業務關係的日方電影人如稻垣浩、辻久一、阪東妻三郎、月形龍之介等的訪華隨筆,同時翻譯一些電影理論、攝製技術方面的文獻,並積極為東方文化編譯館翻譯了為數不少的日本當代文學作品。
抗戰勝利後,此人的行蹤成謎,但類似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因此也希望有人繼續跟蹤,探尋新的線索。
作者:祝淳翔


TAG: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