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 | 城市「權力的文化網路」中的知識分子
原標題:許紀霖 | 城市「權力的文化網路」中的知識分子

▲19世紀的中國鄉紳們
簡介
在革命浪潮到來之前,作為一個自主性的社會有機體,上海這座曾經輝煌過的大都市已經死了,死在了戰爭、內亂之中。

在近代中國城市研究之中,地方社會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杜贊奇在他的名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中,以「權力的文化網路」(culture nexus ofpower)這一分析性概念來描述中國鄉村基層的社會文化網路,並進一步考察國家權力是如何從滲透到破壞鄉村的「權力的文化網路」的歷史過程。那麼:「權力的文化網路」這一概念是否可以用於分析近代中國城市的地方社會?如果可能的話,城市的「權力文化網路」又是如何構成的?本文擬通過研究1900-1937年間上海城市的地方社會,來考察近代城市的「權力的文化網路」,將特別集中於在這樣一個問題:在一個以資產階級為英雄的城市社會之中,為什麼還需要文化精英?文化精英是如何鑲嵌到城市的「權力的文化網路」,與資產階級一起,守護近代上海的地方自主性的?
01
城市的「權力的文化網路」與資產階級
所謂「權力的文化網路」(culture nexus ofpower),是杜贊奇在研究華北農村的基層社會時提出的一個分析性概念。以往的眾多研究都將明清以後的中國鄉村描述為一個士紳階級領導的「鄉紳社會」,杜贊奇獨闢蹊徑,將研究視野拓展到鄉村的文化、特別是大眾文化層面,他提出「權力的文化網路」這一概念,旨在通過對文化及其合法性的分析,觀察權力所賴以生存的社會文化網路,從而重新理解帝國政權、紳士與其他社會階層的關係。按照杜贊奇的解釋,「權力的文化網路」是由鄉村社會的多種組織體系以及塑造權力運作的各種規範所構成,包括宗族、信仰、自願團體以及各種非正式的人際關係網路。這些組織相互滲透和交叉,編織成一個具有公共權威的社會文化網路,鄉村社會的權力控制,正是通過這個網路而得以實施的。

▲ 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
「權力的文化網路」這一分析性框架,與以往「鄉紳社會」的概念相比較,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其一,它並沒有將與國家權力相關的鄉紳視為鄉村社會唯一的地方精英,而是將鄉村的精英視為具有多重來源的複合群,有宗族中輩分較高的族長,有信緣組織中的民間宗教領袖,有公共事務團體的首領,也有各種非正式人際關係網路中的精英。他們構成了領導和控制鄉村社會的精英群。其二,精英們對鄉村社會的控制,重要的不是來自於國家所賦予的自上而下權力,或者精英自身所擁有的各種社會資源,而是精英們如何將這些權力、資源和社會資本轉化為文化的象徵資本,從而在鄉村的文化社會網路中獲得合法性權威。杜贊奇的上述著作之所以在出版之後獲得很高的評價,乃是成功地運用了「權力的文化網路」這一分析性框架,向我們展現了近代華北農村基層社會中多元而複雜的社會文化網路,當這些網路自身比較健全的時候,為國家權力的控制提供合法性支持。而晚清之後當自上而下的的國家權力日益擴張,強加於鄉村社會之上之後,大大破壞了鄉村社會自身的文化網路,最終使得鄉村社會衰敗,中共的農村革命得以發生並取得成功。
當近代中國鄉村社會的面貌越來越清晰的時候,同一時期的中國城市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其是否形成了城市的「權力的文化網路」?中國的城市與鄉村關係,與歐洲頗不相同,中國的城市並非在與鄉村的對抗之中發展起來,在經濟形態與社會網路上,形成了城鄉一體化的格局。按照施堅雅的研究,到中華帝國的晚期明清之際,全國形成了以城市為中心的9大城鄉一體化社會經濟區域網路。城鄉一體化的網路結構表明,原來主要生活在鄉村的儒家的士大夫和商人精英,到了明清之後開始向城市流動,出現了「城居化」趨勢。鄉村精英向城市的集中,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五口通商、沿海、沿江的開放性經濟城市崛起之後開始加速。以江南為例,在太平天國革命到來之際,不僅鄉村的地主、鄉紳逃離鄉土,而且許多農民、手工業者也紛紛向城市集中,形成了第一次城市化的高潮。
城市社會與鄉村社會區別在於,鄉村是一個熟人社會,而城市基本上是一個由各地移民所組成的陌生人社會。當移民們成群結隊來到城市,所帶來的不僅是勞動力和資產,而且是原先在熟人社會中自然形成的社會文化網路。不僅如此,由於城市日益複雜的社會分工所形成的職業分化和文化區隔,在城市居民的內部又形成了新的文化關係網路,縱橫交錯,互相滲透,其內部結構和網路形態遠比鄉村社會複雜得多。因而,無論哪一種政治勢力想要控制城市,都不得不面對地方性「權力的文化網路」,隨著現代化的深入發展,近代中國城市的地方社會不像鄉村那樣日益衰敗,反而在形成和建構之中。

▲城市人口網路
上海作為近代中國最發達和成熟的大都市,從1843年開埠,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到民國的全盛時期1930年代,在城市內部已經形成異常豐富的地方社會網路:一是鄉緣組織,由會館、公所和同鄉會等以原籍地為基礎的區域性移民團體;二是業緣組織,由同業公會、商會、銀行公會、工會、律師、記者、教授、醫生、會計師等以行業或職業分工為基礎形成的同行團體;三是信緣組織,由基督教、佛教、道教以及各種民間信仰所形成的宗教和信仰團體;四是社團組織,由各種學會、教育會、俱樂部等組成的自願性民間社團;五是幫會組織,即擬血緣性的、社會正式體制之外的江湖團體。鄉緣、業緣、信緣、社團和幫會,這些城市內部的社會文化網路,構成了近代上海城市的地方社會,史學界對這些社會網路已經有一些富有價值的研究成果。雖然這些地方性社會文化網路的細節還有待深入研究,但它們之間如何相互滲透、影響和互動,構成一個整體的、流動的「權力的文化網路」,顯然是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
從「權力的文化網路」這一概念出發,我們所關心的是:除了國家權力之外,在近代上海的地方社會之中,究竟誰在控制這個城市?誰在管理地方性公共事務?這種管理和控制藉助於什麼樣的文化權威?他們通過什麼樣的文化象徵符號獲得了地方社會的控制權?顯然,「權力的文化網路」並非與國家權力完全獨立、分離乃至對抗的地方性力量,杜贊奇的研究正是在國家權力對基層如何控制的背景下討論華北農村的社會文化網路。但本文限於主題的限制,將暫時擱置國家權力與城市「權力文化網路」之間關係的討論,而將焦點集中在在近代上海的「權力文化網路」之中,為何在資產階級已經獲得城市控制主導權的情況下,依然離不開知識分子的文化權威的支持?
傳統中國的社會精英由三部分組成:士大夫精英、地主精英和鄉紳。到了近代社會,當社會的中心從鄉村轉移到城市,新式的城市精英便首先在上海、廣州、天津、漢口這些沿海沿江的大城市中出現了,正如白吉爾所說:「在這個城市社會裡,具領導地位的是來源於傳統士紳和商人階級的城市精英階層」。[4]控制近代中國城市的,最初是具有士大夫和商人雙重身份的紳商階層,他們構成了近代中國早期的城市精英。羅威廉通過對清代漢口的城市研究,發現在城市內部存在著一個地方名流群體,他們是由士紳和富商們共同組成的,之後又合流為紳商階層,他們通過與國家權力的密切互動,主導了城市的地方公共事務。雖然羅威廉以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來描述清代城市精英對地方事務的控制這一嘗試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然而正如他在該書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說:「地方社區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做許多事情,他們以地方『公共領域』的名義,創設了帝國政府認為沒有必要、或者只是負擔並可以輕易減省的諸多設施。」隨著城市現代化的發展深入,城市原來的社會階層發生了劇烈的分化與重新組合,士大夫與商人合流成紳商。但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紳商這一過渡性階層又很快消失。握有現代社會最重要經濟與金融資源的資產階級商人,在原來「士農工商」四民階層結構之中,從最末的位置上升到首位,成為主掌地方公共事務的實權階層。而原先排位第一的士大夫階層卻隨著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而發生分化,在清末民初逐步轉型為近代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本身是內部分層非常細密,不同的知識分子之間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參與地方公共事務、介入「權力的文化網路」的程度存在著很大的差別。

▲古代科舉考試
脫胎於傳統精英的近代中國城市精英,來自於三個部分:一是由傳統士大夫轉化而來的學院精英,二是從地主精英脫胎而來的商業精英,三是從鄉紳蛻變而成的地方名流。學院精英主要由一批以大學為生存空間的全國性知識分子,他們所關心的是國家與世界的天下大事,與地方公共事務和「權力的文化網路」基本無緣。在近代中國,這些全國性知識分子主要雲集於北京。商業精英在京滬兩地都存在,因為其所開辦的實業、商業和金融業的關係,他們非常注重地方的公共事務並成為「權力的文化網路」的核心。而城市的地方名流是一個複雜得多的社會群體,他們大部分出身於前述的地緣、業緣、信緣、社團和幫會這幾個城市社會網路。在新崛起的城市精英之中,資產階級扮演了核心的角色,特別在上海這個工商業最發達、社會分工最完整的國際大都市中,擁有經濟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的近代資產階級成為了這個城市的主人,特別在袁世凱死亡之後、南京政府建立之前的北洋軍閥混戰時期,他們藉助手中握有的金融和經濟實力,頻頻干預國家政治。1919年北京爆發五四學生運動,上海資產階級會同其他社會階層,在上海舉行「三罷」(罷工、罷市、罷課),最後逼迫北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不敢在巴黎和會簽字。1921年上海商界與教育界聯合,發起國是會議,繞開南北政府,由民間出面起草國家憲法。而1923年直系軍閥曹錕的北京政變,上海的資產階級拒絕承認,由各商會組成民治委員會,準備實行「國民自決」。凡此種種,都表明在北洋政府時期,上海的資產階級已經登上了政治舞台,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政治階級。
02
為什麼城市資產階級離不開文化的權威?
然而,儘管一夜暴富而崛起的資產階級掌控了經濟和金融的權力,但經濟權力並不等同於社會權威。要在城市「權力的文化網路」之中居領導地位,必須藉助於文化的象徵符號獲得合法性權威,從而更有效地實施權力的控制。「權力的文化網路」的核心問題不是權力在誰的手中,而是如何通過文化的權威而掌控社會權力。在傳統中國的四民社會之中,商人在各個朝代都擁有巨大的財富,這筆財富無論是朝廷還是地方都不敢小覷,然而商人階層並不因此而享有文化上的權威,按照儒家的「重義輕利」觀念和王朝的「重農抑商」政策,富有的商人在正式體制和社會上被人看不起,缺乏與其擁有的財富相匹配的尊嚴和權威,不要說與士大夫比肩,即使在平民當中其社會地位還在農工之下。這一情形到明代以後有所改觀,在富庶的江南出現了紳商合流的趨勢,一方面士大夫的生活開始像商人階層那樣追求奢華,另一方面商人階層向士大夫接近,通過買官獲得功名,在文化上附庸風雅,並參與地方的各種公共事務,通過各種努力,將自身的經濟權力,轉化為文化的象徵資本。
到19和20世紀之交,在開放的沿海和沿江大城市中,出現了一個過渡形態的紳商階層。[6]這一紳商階層,身份雙重,擁有士大夫的功名,經營各種洋務和實業,而且在地方公共事務和國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作用。在晚清上海,紳商階層非常活躍,他們由兩個不同的交往網路組成,一個是以李平書為領袖的上海本地紳商,另一個是以張謇為首的江蘇紳商。上海本地的紳商是清末民初上海地方自治的核心階層,從城廂內外總工程局到自治公所、市政廳,這些前後相繼的上海自治機構領導精英,皆是由紳商組成,而商人領袖占多數。之所以推出李平書擔任自治機構的領袖,乃是他有舉人的身份,有為官的經歷,這些身份使得他比較一般的商人擁有不可比擬的文化權威。不僅商人們推舉他出任總董,而且邀請他擔任多家公司的董事或經理。另一方面,在晚清開始涉足實業和商業的士紳階層,對金錢本身並沒有太大的興趣,他們的真正目的乃是想通過積累財富而擁有更多的文化權威,張謇本人將開辦實業而獲得的利潤大量投資於教育,並與其他士紳們一起建立江蘇省教育會(最初名稱為江蘇學會),總部設立在上海。以江蘇省教育會為中心,從晚清到1927年,構成了一個龐大的擁有文化權威的關係網路,活動涉及教育、實業、地方事務和國家政治方方面面。到了晚清之後,辦教育成為一個最具文化象徵符號的權威來源。江蘇學會的入會條件極嚴,並非一個簡單的行業團體,乃是精英中之精英聚合。根據其會章,會員分為代表會員、志願入會和名譽會員三種,代表會員須由官府推舉,「聲望素為眾所推服者」,志願會員須有會員二人出具保證書或地方教育會出文介紹,而名譽會員則要求更高。

▲張謇
中國與西方不同,雖然在民間底層有豐富的道教、佛教和民間信仰網路,但儒家所代表的道統始終在教統之上,儒家並非宗教,只是世俗化的人文之學,它依靠科舉、書院、私塾等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建制而形成了一個學統網路,儒家的道統就是建立在這一學統網路之上的。從孔子之下的歷代儒家士大夫,無不重視教育,為師者無論在官僚系統,還是在社會底層,皆擁有無可替代的文化權威和道德權威。晚清之際,以科舉和私塾為軸心的舊學逐漸式微,以西學為內容的新學堂取而代之,而各地興辦學堂最積極的,乃是地方士紳,圍繞著興辦學堂、掌控地方的教育權力、進而在「權力的文化網路」之中擁有至上的權威,許多地方的官府與士紳、士紳與士紳之間,都有過激烈的競爭。
清末民初的紳商階層只是轉型時代的過渡性人物,到了1920年前後,近代的資產階級代替了紳商階層成為城市的主角,其標誌性事件,便是該年上海總商會改選,美國留學回來的企業家聶雲台代替了年長的買辦朱葆三,出任新一任會長。1914年之後,中國的城市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新興的城市資產階級無論是實業家還是金融家,都擁有較之前紳商階層更可觀的經濟實力,常常借代發公債、貸款之機會,與中央政府與各路軍閥討價還價,提出政治條件。然而,經濟實力只是純粹的權力,無法直接置換為具有道德價值的文化權威,而在「權力的文化網路」之中,權力是要通過權威而獲得文化合法性的。因此,就像晚清的紳商一樣,新興的城市資產階級也非常注重投資教育,通過教育增加自己的文化象徵資本。聶雲台在當選總商會長之前,就與黃炎培一起發起成立了中華職業教育社。呂芳上指出,五四運動之後,社會各界都意識到學校之重要,各種勢力紛紛介入學校。社會各界辦學之風頗甚,而城市資產階級更是積極。上海的國立大學很少,多為私立大學。私立大學經費來源拮据,往往要靠企業界和金融界大佬支持和輸血。而掌握經濟命脈的資產階級也樂意參與大學董事會,以此博得文化象徵資本。1925年五卅運動之中,部分聖約翰大學的愛國師生脫離聖約翰,另行籌辦光華大學,上海教育界、金融家和企業界名流人士紛紛伸出援手,上海商界實力派人物中,金城銀行行長吳蘊齋、震巽木商公會主席朱吟江、上海總商會會董趙晉卿、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上海銀行公會會長錢新之皆為光華大學董事,在董事會中佔半壁江山。

▲晚清紳商推動經濟發展
在城市的「權力文化網路」之中,擁有文化象徵資本的,除了興辦教育之外,就是主持包括慈善在內的各種地方公共事務。這也是古代中國士紳的重要歷史傳統。梁其姿通過對明清慈善組織的研究,發現各地有聲望的士紳們熱衷於建立善堂,其真正的興趣不在於濟貧,而是教化,通過特殊的施與受的關係,鞏固自己在地方秩序中的道德權威與儒生的中心地位。羅威廉在對清代漢口的城市研究中,也發現了城市的士紳在國家與私人之間的公共事務領域,以社會能動主義的方式建構了一個與歐洲迥然不同的地方管理型公共領域。晚清之後,當紳商階層以及繼起的資產階級成為城市管理和地方自治的主導者之後,同樣繼承了士紳階級的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的歷史傳統。他們明白,無論是教育,還是慈善、救災、維護地方秩序,儘管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精力,但重要的不是付出,而是獲得。僅僅擁有經濟和金融的實力,在城市的「權力的文化網路」並不能擁有征服人心的權威,唯有參與地方的公益事業,積極為民眾服務,才能虜獲人心,獲得在地方社會中的主導權。
然而,主導了城市公共事務的資產階級有一個天生的缺陷,即他們與傳統的士紳以及晚清紳商相比,只是一個擁有權勢的世俗階級,而不具備讀書人在中國社會中那種天然的神聖性和權威性。資產階級富於物質的力量,卻缺乏精神的權威,甚至社會一般人往往對他們存有某種偏見。物質性的資產階級即便是西方名校商科畢業,擁有一流的專業知識,比如上海的金融和實業大亨聶雲台、張嘉璈、錢新之、李銘、陳光甫等皆有日本或美國的留學背景,但他們缺乏的是領導民間社會的話語權,而這樣的話語權則需要有與專業知識不同的博雅之學為背景的。而近代知識分子與傳統士大夫一樣,雖然不擁有任何權勢,卻掌控著主導社會輿論的話語權。於是,城市資產階級縱然一時權傾天下,依然需要聯合文化精英一起掌控地方社會。
上海作為近代中國的社會中心和文化中心,有發達的市場與社會分工,也有影響廣泛的報業、出版業與民間教育,這個城市的知識分子主流並非與社會隔絕的學院精英,而是深刻地鑲嵌到城市社會的媒體精英和社會名流,更確切地說,他們本身就是上海「權力的文化網路」中的一部分。在近代上海,大學、媒體與職場沒有嚴格的界限,職業的流動與交叉是經常性的現象,不少名律師、會計師、醫生和記者受聘於私立大學兼職教授,既賺取一點課時費,也通過學校的師生關係擴展自己的人脈資源。而不少私立大學的教授,也會在外面兼一份工,或者業餘辦書局、當編輯、或爬格子寫作。學術與商業、文化與職場、知識人與市民階級之間,相互滲透、流動和轉換。上海的知識分子與城市社會融為一體,具有鮮明的市民意識和地方認同感,對地方公共事務有強烈的參與熱忱。

▲張元濟
文化與社會的融合,文化精英與工商各階層的緊密互動,成為上海城市社會的一大特色。張元濟是商務印書館的主持人,他所交往的圈子,除了學術文化界人士,還有一批熱心扶助文化事業的實業家和金融家,如聶雲台、穆藕初、錢新之、簡照南等等。張元濟有自己的啟蒙理想,但與北京頗成異趣。北京是中國的學術中心,精英文化憑籍的是北大、清華等著名國立大學。上海是全國的文化中心和輿論中心,最有影響力的報紙、發行量最大的書局、品種最豐富的雜誌都雲集上海。報紙、雜誌和出版業,構成了近代的傳播媒介。傳播媒介與大學不一樣,大學吸引的是文化精英,而媒體面向的是各類社會大眾。北京的啟蒙是精英對精英的啟蒙,走不出精英的圈子;而上海的啟蒙,則是精英對大眾的啟蒙,通過媒體的管道,訴諸於公共輿論、教科書和流行讀物,直接面向社會公眾。上海的精英文化與啟矇事業,不是一個精英向大眾佈道的單向過程,而是精英與大眾的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的雙向過程。於是,在上海文化之中,精英與大眾、啟蒙與生意之間,並沒有一條絕對的界限。張元濟主持的國內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商務印書館,在民國初年的啟蒙運動之中,它的影響力絕對不在北京大學之下。商務印書館走的不是上層而是下層路線,它出版了大量的辭典、教科書和通俗學術性讀物,將新科學、新學科和新知識傳播於社會,它所創辦的雜誌系列:《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婦女雜誌》、《青年雜誌》、《小說月報》、《自然界》等等,除《東方雜誌》面向知識界之外,其餘都是面向特定的社會大眾,走市場路線,卻絕不媚俗;教化大眾,卻不居高臨下。1930年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共計2000卷的《萬有文庫》,收集有各種中外的經典讀物,以簡裝、價廉的方式面向一般讀者發行,其工程之大超過法國啟蒙學派的百科全書,在文化效益和市場效益上取得了雙向成功。
不惟出版業,連上海的教育,也面向平民,黃炎培與一批實業家創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與為學術而學術的北京國立大學的辦學理念迥然不同,乃是面向市場、面向社會,以 「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為辦學宗旨,帶有強烈的功利主義色彩。職業教育如此,連上海眾多的私立大學的辦學傾向也多傾向實用主義,商科、會計、醫科和應用法律專業較之北京不僅數量要多,質量也在後者之上。上海的教育和出版業,因為直接與市場接軌,與城市的市民階層息息相關,本身就構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鄒韜奮從聖約翰大學畢業之後到中華職業教育社主辦的《教育與職業》任編輯,編譯的第一本書是英文的《職業智能測驗》。當譯成中文之後黃炎培將他叫到辦公室,嚴肅地告訴他,編譯的時候不要忘記重要的服務對象是中國的讀者,在編法和措辭方面一定要處處顧到讀者的心理和需要。這給年輕的韜奮很大的刺激,後來他主編《生活周刊》,定位在為平民階層服務,代表平民階層說話,取得了巨大成功,發行量直逼《申報》,以至於為南京的國民政府所忌恨,最後被禁郵、查封。

▲鄒韜奮
03
鑲嵌於城市「權力的文化網路」的上海文化精英
在近代上海的城市文化精英當中,史量才與黃炎培最具典範,一位是《申報》的老闆,另一位是職業教育的創始人。史量才畢業於杭州蠶業館,黃炎培在南洋公學肄業,如果從純粹的知識分子的標準衡量,似乎都不太純粹和典型,但這兩位從底層奮鬥出來的地方名流,恰恰成為上海文化精英的標杆性人物,證明上海灘不在乎學歷,只相信能力。史量才和黃炎培在清末民初都屬於張謇為首的江蘇省教育會圈子,這個圈子在上海和江蘇擁有很高的文化權威和廣泛的社會資源,他倆通過這個圈子逐漸積累自己的人脈關係和社會象徵資本,黃炎培長期擔任江蘇省教育會握有實權的副會長,史量纔則在張謇等人的支持下,買下了《申報》股權,一躍成為上海灘的報業大王。這兩位民國期間上海地方名流中的領軍人物,史量才既是具有現代新聞理念的職業新聞人,同時又涉足金融業,創辦中南銀行;黃炎培在掌控江蘇省教育會的同時,又聯合教育、金融和實業界實力派人物,創辦中華職業教育社,並受史量才邀請,參與《申報》的輿論設計與事務管理。他們以《申報》、江蘇省教育會(後期為中華職業教育社)為中心,通過輿論和教育的文化象徵資本,編織了一個涉足教育、媒體與金融的社會網路,擁有豐富的人脈資源,在城市的「權力文化網路」之中,具有舉足輕重、不可代替的地位。
上海的文化精英是多元的,在近代中國城市當中,組織化的程度也最高。新聞界有新聞記者聯歡會,教育界有上海各大學教職員聯合會,法律界有上海律師公會,經濟界有上海會計師公會……這些都屬於法律所認可的職業團體,此外還有處於合法與非法邊緣的、不被政府所承認的政治性團體,如1935年一二九運動之中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這一組織成為日後席捲全國的救國會運動的始作俑者。

眾多的文化精英職業團體所構成城市的社會網路,在城市公共事務中未必都擁有文化權威和支配性權力,真正處於支配性地位的,除了上海總商會和銀行公會之外,乃是江蘇省教育會。曹聚仁1960年代在悼念黃炎培文章中如此回憶他剛到上海的情景:
到了上海,我才知道江蘇教育會是了不得的。那位南通王張季直在江蘇是太上皇,北洋軍閥任何勢力,非張氏點頭不可。孫傳芳所以能做五省統帥在江南立定腳跟,就是他們所支持的。地方割據,不管誰來稱王,教育、財政、實業這幾個部門,總是轉在他們手中;黃氏便是那一派的吳用。江蘇教育會在上海西門有宏偉的會所,還有中華職業教育社。此外,如商務、中華這幾家大書店,和《申報》、《新聞》、《時報》這幾家大報館,和他們互通聲勢,真的是顯赫一時。
從清末到民國,從張謇到史量才、黃炎培,江蘇省教育會以上海為中心,向全省輻射,形成了影響江南社會一個龐大的「權力的文化網路」。前已敘述,在近代社會,教育是最具有權威的文化象徵資源,誰掌控了教育,誰就擁有了社會的道德權威,而這一權威足以與朝廷權威比肩抗衡。太平天國之後,地方士紳的權力崛起,籌辦洋務、興辦教育,無不靠地方士紳。張謇作為江南士紳的精神領袖和實力人物,在晚清擁有無人可替代的崇高權威,這是一種「無權者的權力」。在他的布局之下,江蘇省教育會、預備立憲公會和江蘇省咨議局的核心成員高度重合,形成三位一體,儼然是一民間的政治中心,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在此發起,武昌首義之後,又邀請南北政府代表,在上海的惜陰堂和談,最終促成了清廷遜位、中華民國成立。到民國初年,江蘇省教育會的勢力進一步擴張,雖然張謇逐漸淡出,但新一代領導人袁希濤、蔣維喬、黃炎培、沈恩孚、郭秉文迅速登上歷史舞台,在民初政治中叱吒風雲。曾經為江蘇省教育會會長的袁希濤出任教育總長,史量才以這個圈子為背景,先後買下《申報》、《新聞報》,成為中國報業中執掌牛耳者。黃炎培又聯合上海的工商界大佬聶雲台、穆藕初等,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而郭秉文擔任東南大學校長,把東大辦成與北大齊名的東南第一學府。江蘇省教育會不僅掌控江蘇省中小學的人事任免權、南京的東南大學和上海的暨南大學,而且與北京政府、地方當局、各路軍閥、政界、金融界、實業界、報界和出版界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自身的勢力也滲透到這些領域。因此被國民黨視為「江南學閥」,在1927年北伐軍到上海的時候通緝他們,黃炎培被迫流亡日本。江蘇省教育會解散之後,黃炎培轉以中華職業教育社為中心在上海展開活動,加上史量才所掌控的上海媒體輿論話語權,憑藉幾十年間在政界、商界、文化界積累的人脈資源,繼續在地方與全國的公共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海的文化精英有強烈的地方認同和地方意識,他們與城市的紳商階層和資產階級聯合,積极參与到上海的地方自治之中。在前述的1905-1914年第一波地方自治高潮之中,李平書作為一個擁有社會聲望的官僚士紳,始終執掌上海地方自治的牛耳。到1923年到1927年的第二波高峰,江蘇省教育會的袁希濤、黃炎培、沈恩孚等作為新崛起的文化精英,深入介入到地方自治運動之中,成為其中的中堅力量。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之後,國民黨十分重視上海這個最重要的國際大都市,將其置於國家權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地方自治機構上海市公所遂告解散,地方自治運動遭到重大挫折。儘管如此,由於這個城市的資產階級、文化精英和各界人士組成的地方社會依然存在,而且頗具實力,因此無法抑制地方的自主性衝動。1932年「一二八」抗戰爆發,資產階級與文化精英藉此機會,聯合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援助十九路軍抵抗日軍。戰爭結束之後,維持會並沒有解散,在國民黨地方當局默許之下,改組為上海地方協會,史量才出任會長,幫會領袖杜月笙、商界領袖王曉籟擔任副會長,黃炎培出任秘書長。會員當中,實業界、金融界和商業界的實力人物佔據主流,也有一批上海著名的文化精英,有知名會計師潘序倫、徐永祚,有聞名滬上的醫學權威顏福慶、龐京周、牛惠生,有大學校長褚輔成、郭秉文、楊志雄、吳經熊、劉湛恩,有《新聞報》經理王伯奇等等。
上海地方協會作為一個由地方名流組成的民間團體,雖無地方自治之名,卻有地方自治之實,其功能表面是協助政府從事社會救濟、慈善和公益事業,但這些地方名流卻表現出強烈的擺脫南京政府控制、追求地方自主性的利益衝動。尤其是史量才擔任會長,黃炎培擔任秘書長,使得地方協會在利益衝動之外,還有要求抗戰和民主的政治理念。在文化精英的領導下,以上海的資產階級為實力後盾,多次向南京政府發難,抵制政府召集的國難會議,發起廢止內戰大同盟……1930年代初這些以上海為中心的運動,其背後都有上海地方協會的身影。而以史量才為代表的上海文化精英,扮演了核心的作用。對一個專制的獨裁者來說,最可怕的對手除了政敵之外,便是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所聯手的社會力量,這種以市民社會為後盾的公共領域,有經濟實力,又有公共輿論,是蔣介石最為忌諱的,必欲除之而後快。後來蔣派特務在滬杭公路上暗殺史量才,所針對的不是史個人和《申報》,而是整個上海地方社會。
近代上海作為全國的社會中心和文化中心,無論是城市資產階級還是文化精英,其關切點除了地方利益之外,同時還有國家政局。這個城市對於他們來說就是存在的家,家國天下是命運共同體,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也是全國的上海和世界的上海。近代以來政治格局所形成的南北分立,上海儼然是京城之外的第二個中心,慈禧太后宣布對八國聯軍宣戰的時候,南方的封疆大吏以上海為後盾宣布「東南互保」,彷彿另一國度,置身於戰爭之外。辛亥革命席捲全國,南北政府對峙,又是在上海舉行南北議和,最終催生了清帝遜位、民國誕生。五四爆發學生運動,讀書人與北洋政府相持不下,又是上海的教育界與商界聯手,發起「三罷」,迫使北洋政府不敢在巴黎和會簽字,罷免了3位賣國的政府官員。1935年北京爆發一二九學生運動,上海各界立即跟進,成立救國會,將單純的學生運動擴張為全民的愛國運動。由此可見,北京作為學術中心和政治中心,往往得風氣之先、感覺最敏銳、走在時代最前線的是大學生,而學生的背後是學院精英的支持。但學生運動的特點是來勢洶湧,卻無法持久,在這個時候,上海的呼應與接力就顯得分外重要,學生運動蔓延到上海,便超越學界,擴展到整個社會,並震撼全國和全世界,成為波瀾壯闊的全民運動。北京是公共領域的中心,以知識分子為首;上海是市民社會的大本營,以資產階級為代表。近代中國的社會運動,通常由知識分子發動,隨後由社會各階層跟進參與。運動往往從北京開始,在上海燎原,並最終獲勝。

▲一二九學生運動
在1920-1930年代上海幾次重大社會運動當中,雖然城市資產階級扮演了主角,但到處可以看到文化精英活躍的身影,他們憑藉鑲嵌於城市「權力的文化網路」中的文化權威,與資產階級聯手,上演了一出又一出震撼全國的好戲。1919年北京爆發學生運動之後,5月7日上海在西門外體育場召開國民大會聲援北京,被公推為大會主席的,是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在隨後的「三罷」運動當中,在社會上擁有廣泛人脈關係的江蘇省教育會異常活躍,串聯社會各界,成立了上海工商學工報各界聯合會,參與領導上海的六三運動。1920年代初的國民大會運動,則是在蔡元培的提議之下,由商界的聶雲台和教育界的黃炎培主持,舉行商教兩界聯席會議,議決發起全國八團體國是會議,邀請張君勱草擬國家憲法草案,向北洋政府施加壓力。而1935年底的救國會運動,更是上海激進的文化精英取代了黃炎培這些溫和的地方名流,成為領導運動的中流砥柱。最早成立的是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然後跟進的是婦女救國會、大學教授救國會、職業界救國會、新聞記者救國會、學生救國會、工人救國會等社會各界。當運動迅速席捲全國的時候,又是上海文化精英在滬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隨後遭到國民黨政府逮捕下獄的救國會「七君子」領袖之中,沈鈞儒、史良和沙千里是律師,鄒韜奮和李公朴是出版界人士,王造時是大學教授,章乃器是金融界人士,這表明了新一代上海文化精英身份上的多元性,而走在最前列的,竟然是沈鈞儒為首的律師界和韜奮為代表的接近社會底層的文化界人士。在救國會運動期間,上海的工商金融界頭面人物都沒有出面,只是在後台充當幕後支持者和與政府之間的調停人。上海這座城市的英雄角色,又一次回到了知識分子那裡,只是這一次擔當主角的,已經是另一批更年輕、更激進的城市文化精英。
從1900年到1937年,上海的文化精英聯合資產階級,在近代中國風雲變幻的大時代中,建構起一個城市的「權力的文化網路」,這一網路憑藉由各種社會關係交錯而成的城市社會,與國家權力有著既互動又抗衡的微妙聯繫。掌控上海「權力的文化網路」的,是一批城市的地方名流,他們當中有文化精英,有實業界、商業界、金融界人士,也有幫會領袖。他們周旋於中央權力與各種政治勢力之間,藉助多元權力的孔隙,控制了上海的城市社會。同樣是「權力的文化網路」,近代的城市社會與傳統的鄉村社會是有區別的。在鄉村社會之中,士紳始終是主角,但在近代城市精英之中,核心已經讓位於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成為上海這個城市的英雄,像史量才這樣的報業大王,既是知識分子,又是資產階級,沿承晚清紳商的傳統,具有亦紳亦商的雙重身份。從清末到1930年代,上海的文化精英與資產階級的戰略同盟,艱難地堅守著這所城市的地方自治,即使在國民黨一黨zhuan制時代,也有頑強的表現。他們的內心充滿了家國天下之情懷,這個家園,便是有著強烈認同感的上海這所城市,擴展開去,演繹為國家和天下意識。因此,上海的城市精英,不僅在堅守一座城市的地方自主性,而且以上海的市民社會為後盾,以攻為守,積極地過問國家公共事務,試圖影響和改變中央政府的國策。

▲近代文化精英階層
遺憾的是,1937年之後,首先是日本侵略的炮火,然後是國共內戰的硝煙,徹底摧毀了上海的經濟基礎和地方精英。企業和商業的凋敝、國家壟斷資本的擴張和惡性的通貨膨脹,使得上海的資產階級元氣大傷,不得不依附於國家戰時體制而苟延殘喘。他們不再像當年那般風華正茂,雄心勃勃,不復成為城市的英雄。而城市的文化精英,在戰後雖然因為擁有輿論的主導權而一度如日中天,但國共內戰一爆發,他們便失去了仲裁和制衡的力量,而且因為失去了資產階級以及城市的「權力的文化網路」而變得力量空虛,徒有聲勢。到1940年代,被戰爭和內戰摧殘得奄奄一息的上海,這所城市的內在能量業已掏空,資產階級與文化精英各奔前程,各謀其路,往日的戰略同盟不復存在,城市社會迅速解體,「權力的文化網路」千瘡百孔。而各種意識形態、黨派勢力深入地滲透到城市的肌體當中,城市自身的免疫功能和社會基礎走向崩塌,一場革命正向這座城市席捲而來。事實上,在革命浪潮到來之前,作為一個自主性的社會有機體,上海這座曾經輝煌過的大都市已經死了,死在了戰爭、內亂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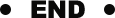


TAG:思想的蝙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