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為阻止北京知青返城回京,竟採取限制北京知青購票的做法
原標題:延安為阻止北京知青返城回京,竟採取限制北京知青購票的做法
1969年3月底的陝北,春天姍姍來遲,幾場小雨過後,大地返青,萬物復甦,早晨陰霾的浮雲掩住了太陽,翠綠的山間飄浮著團團霧氣。
打早收工回來剛吃過早飯,「哎,兄弟,你的信。」看著信封上久違了的熟悉字體,心跳驟然加速,這分明是身陷「牛棚」中的父親寫來的信。咋,「解放」啦,能回家啦?三下兩下飛快地讀完了來信。嘿,果然不出所料,老爹獲「解放」能回家了。我點起顆香煙,平靜一下心情,梳理一下思路。想起現實中全家六口人天各一方的境遇,自「文革」開始父親就飽受磨難,歷經打倒、批判、游斗、抄家、扣工資,直到只發生活費,隔離在「牛棚」中已過年余。而家裡的生活就僅靠母親一人支撐,過得辛苦!我插隊離京前也沒能和關在「牛棚」中的父親見上一面。哥、姐兩人或隨單位遷徙外地或到內蒙古農區插隊,母親報名去單位幹校純粹只是為了能使我避開插隊帶我同行。然而命運多舛,在我離開北京十天後,她去幹校的申請才被批准,現母親已到河南信陽羅山機械院幹校,在京留守的就只剩七十多歲的外婆一人。插隊離京前夜母親對我說的「家裡只能給你這三十元錢了,可要省著點花」這句話至今還餘音在耳。轉而又想到年初剛插隊進村時我們曾在忠貴家吃過派飯,忠貴媳子還親自給我們做過飯吃,現時未隔多久,忠貴媳子的音容笑貌猶在,人咋就沒了?哎!真是人生苦短,只有親情最重要!抬頭間猛然看到牆上掛著的主席詩詞:「……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哎,咱也要只爭朝夕,回北京與家人團聚去!我狠狠地摔掉香煙,一骨碌站起來,開門出去。
門外懶洋洋地卧著一條不知從哪兒來的黑狗,正巴結討好地望著我,我走近前無端地朝黑狗猛踹一腳,黑狗憑空遭此攻擊,無辜地邊嗷叫著邊狼狽地夾起尾巴逃走了。我痛快、解氣地哈哈大笑起來。
數數看,還剩多少錢?我翻箱倒櫃地把行李翻了個遍,連毛票帶鋼蹦兒,也就只湊出十來塊錢,「這點錢也就夠到西安的,回趟北京起碼要三十塊,這差的碼子還大著哪,咋弄?」我心裡琢磨著,借錢?周圍這幫人,大家都窮哈哈的,買盒「羊群」還磨蹭半天的主兒,再說即或借了,過後又拿啥還啊!跟家裡要?咱也十七歲五尺高的漢子,出來闖天下的爺們兒了。家裡啥情況,又咋能開口?突然想到如果把我下個月的分內口糧(當時國家規定撥給每位剛下鄉知青前十個月的定量口糧,以支持知青到秋後,然後再憑工分分口糧,自食其力)糶了,這不就有錢了嗎?得嗬,就這麼辦!
很快我就摸清了如何充分利用這有限的資源,並使之收效最大化的途徑。先設法取得一份公社開的回京介紹信,再憑此介紹信去茶坊糧站把當月國家配給的買糧款及相當於四十四斤成品糧的糧油額度以全國通用糧票的形式領出來,再把全國通用糧票按每斤三毛的行市價,由村裡的瘸子學兒找人糶給茶坊鎮上的包工頭兒。發給知青的買糧款和糶糧票的錢兩項加起來就是四十四斤口糧糶得十六塊多錢,再加上原有的十二塊多錢,差點也不多了。顯然這是條環環相扣的「連環計」,關鍵是如何能蒙得公社介紹信?不慌,先踩點調查調查再說。經過幾天串隊交流、實地觀察,嘿,天無絕人之路,有門了!裝病到縣醫院開份回京檢查證明,拿著縣醫院的回京檢查證明,再到公社去轉開回京介紹信。而這又絕對是最簡單可行的捷徑。能行!就這麼干。
轉天先奔城裡縣醫院探探路。洛河由北向南流經茶坊西側後轉個彎繞過縣城東北角轉向正南,茶坊與縣城間是片布滿卵石和河沙的沙梁,一條彎曲的小路穿過乾涸的河床沙地直通縣城。美中不足的只是過洛河無橋,全靠自己拉繩坐擺渡船過河。縣城邊洛河兩岸橫拉著條粗纜繩,繩下拴著條能載十來口人的木船,兩岸要過河的人就全靠站在船上像拔河似的一把一把地拉著纜繩渡船過河。但這肯定要比走通土橋的大路至少近五里路,是條省時省勁的捷徑。
坐落在城圈兒里的縣醫院是由數排刷了白石灰的平房組成的。而平房的門窗都被漆成天藍色,幾位穿白大褂的人進進出出,還有就是四鄉來的病人,其中不乏由架子車拉來的重病號。醫院裡還有幾位頭破血流的知青,被同夥簇擁著,在醫院裡像沒頭的蒼蠅似的逐屋亂竄,這是知青各幫派間「茬架」的結果。在醫院的角落裡,我與幾位懷著同樣目的的外校知青不期而遇,眾人一拍即合,與他們交流過後,取得了「真經」,就按他們的方法辦!
幾經奔波,又幾經周折,在5月中旬的一天,我如願以償地得到了介紹信。要知道在當時如果沒有公社一級的回京介紹信,不僅換不到糧票,就連去銅川的長途汽車票都買不成。而延安地區(今延安市)為阻止北京知青返城回京,竟採取限制北京知青購票的做法,對無公社介紹信的北京知青一律不予售票。而拿到了公社介紹信,也就意味著我回京的願望終可實現了!餘下的事情,就是技術層面的工作了。雖然費力,但卻能逐一實現,這裡最關鍵的還是如何能湊到起碼的錢!常言道:「一分錢難倒英雄漢。」真為這事熬煎。一天我和玉林同在茶坊街上的廁所方便,當他聽說我下一步準備回京時,這老兄毫不猶豫地從上衣口袋中摸出一把「碎銀子」,不由分說地硬塞到我的手裡,「窮家富路,拿著,多少也管點用」,雖說只有兩塊多,但他仗義疏財的慷慨之舉,令我感動,他的行為對我產生巨大影響,並使我記憶至今。這裡的廁所多是土牆打造、露天設置並條件簡陋,衛生惡劣且氣味熏人。廁所內群蠅飛舞、蛆蟲攢動的景象令人觸目驚心,更有豬狗時常無端「光臨」覓食,直驚得方便之人防不勝防亦轟趕不及。此間的便坑中卻絕少紙跡,常見有些許沾滿糞跡的胡基(土坷垃)或玉米葉等散落其中,而四圍土牆轉角的下半截經常糞跡斑駁或坑窪殘缺,對此我一直百思而不得其解。直至某日,我看到一位鄉黨如廁起身後,遍尋胡基未果,竟神色自若且旁若無人地依在牆角邊棱處蹭起來,方才恍然悟出其中奧妙。
5月底的一天,我如願搭上來自延安途經茶坊南下銅川的長途汽車,緊張數日的心情稍事放鬆,終於踏上了回家的旅途了。我鬆了口氣,隨著汽車的啟動,望著車窗外逐一經過的川口、史家坪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村莊、農舍和正在田野里下苦勞作的人群,似夢似醒幾乎不敢相信:回家!這夢想成真的事,竟一步步地接近現實了。
汽車向南吃力地爬上交道塬,又經几上幾下的數次顛簸,中午時分汽車停進了洛川站。隨即上來五位知青打扮的青年,為首的是位著銅紐扣、立領深藍色鐵路制服的哥們兒。眾人交談後得知他們是丰台鐵路某中的鐵路子弟,此擬去銅川扒火車回京。太好了!這與我的意願不謀而合,同車還有兩位在延安上車的知青,大家遂結伴同行。
汽車到銅川後,氣溫明顯較陝北熱了許多,我們已顧不得吃飯和觀光,印象中只感到銅川髒亂差得出奇,狹窄的街道上人來車往亂糟糟的,街面上塵土伴著煤灰隨風四處飛揚。眾人急奔火車站,剛好趕上趟車票只有客票半價的悶罐車去西安。眾人原想用站台票矇混上車未果,只得各自破費一塊多錢買票上車。悶罐車原本是貨車,車廂里並無座位,只是臨時鋪些稻草,又用磚頭壘起幾條方木,權充座位,僅此而已。
我們上車方才落座,汽笛長鳴,列車已慢悠悠地動起來了,眼瞅著車窗外景色向後逝去,卻感覺車速比幾個月前來時快了許多,隨著列車有節奏地搖擺,眾人竟在昏然中各自睡去。不知過了多久,突然間,火車急劇地震動,車速明顯慢了下來,似乎在彎道中緩慢蛇行,後來才知道這是富平莊裡一帶,這一帶地域在地理上正處陝北高原的最南端,再往下就進入八百里秦川——陝西的糧倉、豐腴的關中平原了。後據當時在富平插隊的西安知青、我的西大同學趙許直講:秋收後他們扒煤車回西安,就在這一帶減速下坡時,坐在煤車頂上的他們突遭農民胡基的攻擊,他們反應迅速地用大批的煤塊奮力還擊。煤車過後,他們驚異地發現,農民們不知從哪兒摸出條布袋,正在撿拾他們扔下的煤塊,他們這才恍然悟出農民用胡基攻擊他們的真實目的。嘿,這兒的農民也,忒靈醒(機靈)啦。
「西安到了,下車、下車……」乘務員逐車廂吆喝著,一打聽去北京的80次列車已經開走了。咋辦?大家早已是飢腸轆轆了,先填飽肚子再說,於是我們隨著下車的人流出了西安站。
久違了的街燈、無軌電車、殘缺的標語牌和各色人等這些大城市特有的景象,裹挾著悶熱、骯髒的空氣,伴著喧囂的雜訊不由分說地撲面而來。馬路上各種車輛互不相讓地混擠在一起,喇叭聲響成一片。幾輛拉煤的「狗騎兔子」三輪貨車噴著黑煙,單缸柴油機發出「突、突」的巨大雜訊,也湊熱鬧地混跡其中,更是給本來就擁擠的街道添亂。西八路口左邊晝夜營業的吃食店裡人來人往進進出出十分熱鬧,我們隨著人流拐進一家擁滿了人的麵館,燈光下大批的蚊蠅飛舞,驅趕不贏。餐桌上是許多無人收拾的臟碗,但卻幾乎沒有座位,食客們只能或站或蹴著進食。我買票排隊好不容易搶到兩碗面,找了個桌角才勉強把它們安頓下,在狼吞虎咽中吞下第一碗面後,第二碗端上手才扒拉了兩口,突然感到有隻小手在扒拉我的胳膊,扭頭一看,有位垢面婦女抱著個臟乎乎的要飯娃,一隻掉了瓷的大號搪瓷缸子直伸到我眼前,「看娃恓惶的,給娃吃上嘴嘛。」得嗬,全給她啦!
「哥兒幾個,快走。」洛川兄弟一手抱著一摞麵餅,一手拎著個軍用水壺,「打聽過了,待會兒咱們去西安東找奔東的貨車,准沒錯。哎,誰再去找點鹹菜。」工夫不大,眾人在站前廣場正中高大的主席像腳下重又聚攏起來。沿著鐵路走,這辦法雖原始,但最有效,一準能找到西安東站。
從地圖上看,隴海鐵路是條東西走向橫貫關中的直通線。西安站是客運站,左行西進的貨車,在西安西站編組發車,而右行東進的貨車,則由西安東站編組發車,這可是有哈數(規矩)的啊。但即使在西安東站發的車也會有例外,記得當年我家鄰居同在富縣南道德插隊的王小明,就曾和我講過他的經歷:他們一伙人在西安東站不問青紅皂白,見了掛著機車頭的火車就往上爬,結果扒上趟煤車,原指望搭上這車起碼到鄭州,正在高興之餘,未曾想這趟車開了沒多久,竟拐彎奔了東南,這隴海線咋拐了彎?這夥人正在納悶中,沒過一會兒這煤車就到了地方。嘿,敢情扒了趟發給灞橋熱電廠的煤車。結果這夥人又沿著來路走了三個多鐘頭折回西安東站。哈哈,這夥計可直夠背的!
我們八個人順著鐵路邊走邊打聽,又走了起碼兩個小時,西安東站終於呈現在我們眼前。在人造「小太陽」——疝氣燈慘白燈光的照耀下,一道稀疏的鐵絲網背後靜卧著十幾條泛著幽幽藍光的鐵軌。
我們鑽過鐵絲網進了調車場,在一幢值班室模樣的單間平房面前停住了腳步。房前用混凝土構件支起的葡萄架上纏繞著翠綠的藤蔓,一根龍頭上捆著鐵絲的自來水管突兀地立在牆邊,湧出止不住的漏水,滴滴答答地匯成小溪,我們正好喘口氣,先洗把臉,休息一下,再把水壺灌滿。
看著靜卧在軌道上的大批空車廂,正在猶豫搭哪趟車時,「丁零零……」忽聽得一陣自行車轉鈴聲,抬眼望見一位穿著鐵路員工制服的年輕人,騎著一輛嶄新的自行車,正很得意地從我們面前經過。「站長,這趟車去哪兒啊?」洛川兄弟中有位乖巧地不失時機地發問。「去鄭州,等信號就發。」啊!竟有這等好事?
眾人喜出望外,趕緊的,我們直奔守車。守車裡黑洞洞的,啥也看不見,我一腳踩上個軟綿綿會動的東西,著實嚇了我一跳。劃根火柴一看,原來有兩個要飯的花子早已捷足先登地佔了守車,這哪能行?我們仗著人多勢眾,三下兩下就把他們轟下了車,還未等坐穩,眾人忽然聞到空氣中惡臭異常。「哎喲!這要飯的真XX缺德,「丫還在這兒拉了泡屎!趕緊轉移。」眾人又從守車上急急忙忙地躥了下來,恍惚間看見剛才那騎新車的年輕人手持「李玉和」式的信號燈從值班室內走了出來。快!已無選擇餘地,從守車向前又跑了四五節車廂。「別太朝前,小心落煤灰。」洛川兄弟果然經驗老到,在他的帶領下,大家就近找了節高幫車廂爬了上去,才站穩,「咣當」一聲,列車編組前端的蒸汽機車頭喘著粗氣已撞上了鉤。又過了一會兒,只見列車編組後邊的值班室那邊綠色的信號燈在空中連續畫著大圓圈。「要走啦!」深諳其道的洛川兄弟已悟出其中的門道。說話間,汽笛聲響,列車突然向前一躥,巨大的慣性,使我猛然向後一個趔趄,幾乎摔倒,幸而被洛川兄弟一把扶住。但火車總算是慢慢動了,向東走起來了,望著鐵路兩旁一簇簇閃爍著紫光和藍光的信號燈。嘿,這下離家真的又近了一步!
蒸汽機車頭噴著黑煙,喘著粗氣,牽引著四十多節各式空車廂緩緩向東,駛離西安東站,這已是後半夜了。我站在空曠的車廂中,四下眺望,城市特有的喧囂聒雜訊被列車行進中有節奏的相互撞擊聲所替代,西安很快就消失在身後。四周重又陷入黑暗,漆黑的夜空中繁星閃爍,遠處點點的燈火慢慢退去。隨著列車逐漸加速,溫暖濕潤的晚風迎面吹來,不知不覺中大家竟相互偎依著各自睡去。也不知過了多久,矇矓中我被凍醒,此時天已大亮,開車時還溫暖濕潤的晚風此刻已轉為無孔不人的凜冽寒風,只見其他幾位都畏縮著團在一起,另有兩位則圍著車廂跑圈取暖。「到哪了?咱們方向對嗎?」我起身問道。「方向沒錯,剛過渭南。」一直在注意觀察的洛川兄弟答道。「渭南在哪兒?」我有點搞不明白。「哎,快看,這是幹啥的?」大家都伸長了脖子探頭向車南邊望去:火車正從一座架著挺機槍的哨位前經過,不遠處一座巨大的石頭山已被削去了大半,裸露的岩石顯出黃白的本色。依山而立的高大標語牌上白底紅字地寫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類的口號,一群身穿寬藍白條服的人正拉著架子車搬運著石塊。看樣子這是個勞改採石場。蓮花寺,一晃而過的小站地名,告訴我們這裡的確切位置。後來才知道蓮花寺就是陝西省二監的所在地。
列車又東進開行了不知多久,但常識告訴我鐵路右側高聳入雲、連綿不斷且險如刀鋒似的石頭山峰,應該就是著名的西嶽華山。
「拿著,先墊補點東西。」洛川兄弟伸手遞過張麵餅來。嘿,他們真不愧是鐵路子弟,「道上」的事都想得那麼周全。不服不行!
火車終於在孟塬停了下來。孟塬是西安鐵路局出省前換機車頭或補煤、加水的最後一站。我們也趁機從高幫車廂里爬了下來,紛紛溜到站台上活動活動身子,順便再找有水的地方洗把臉,方便一下。我發現不遠處有賣煮白薯的,於是買了一堆捧回來,請眾人分享,也算是對大夥一路相互關照的感謝。
隨著一聲汽笛,列車又重啟動向東開進,這時太陽早已熱辣辣地高懸在半空,早起的冷風也變得乾熱起來,風似熱浪般的吹襲在臉上、身上,毫不留情地帶走殘存的水分,剛才在孟塬洗臉時蘸濕了的毛巾,轉眼間就像被吸幹了水的蔫蘿蔔,僵硬地斜掛在書包上。火車過潼關後開始鑽隧洞,隧洞裡面黑乎乎的,煤灰和著巨大的反射雜訊,劈頭蓋臉地裹挾而來,煤灰把眾人嗆得一塌糊塗,無奈間只有緊裹起衣服蜷縮著身子,緊緊地躲在車廂角落裡。接著雜訊減弱,周圍又明亮起來,這是出隧洞了。轉眼間又鑽進第二個、第三個……這樣的經歷一波接一波地交替輪迴著,經過多次循環,也就是鑽過了多個隧洞。果然,洛川兄弟說得不錯,我們坐的車廂因為靠後,煤灰大部分都落在列車編組的中段一帶,但即使如此,我們亦不能倖免,只是比其他車廂少落些煤灰而已。
列車經過隧洞群後進人河南地界,周邊的景色與陝西相比除山矮了些,窯洞、廈子這些有西北地域特色的民居少了些外,看不出再有其他什麼明顯的不同。站在行進的列車中順著車廂向前望去,我不由得大吃一驚!幾乎每節車廂里都載有搭便車的各色人等,甚至連擔大籮筐賣小雞的小販和看起來似乎是串門走親戚的老太婆也都在其中。天知道這些人是何時、何地、用何種方法搭上這趟列車的,火車的去向及停靠這些人又是咋知道的?這些疑問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心中充滿了疑惑。
中午時分列車停站三門峽西。就聽「咣當」一聲,哎喲,壞啦,車頭咋摘鉤開走啦!難道這些車皮就甩這兒不管了?眾人議論紛紛,是等著掛頭再走還是跳車?誰也拿不準主意。忽然隨風傳來斷斷續續的廣播喇叭聲。「哎,都靜靜,聽聽廣播說什麼。」洛川兄弟吆喝住眾人。「送親友的……同志請注意,開往青島的XXXX次列車……就要開車了……請下車。」嘿,天無絕人之路!咱們轉移陣地去蹭那趟車。眾人紛紛翻身爬下貨車,向北越過條條鐵軌,直奔停在北站台南側的刷著綠漆的客車。不知何故客車編組中有節車廂鐵路兩側的車門全都大敞著,這正好使我們有機可乘,從而避開站台上檢票員的視線,我們從靠南側的車門全都順利地溜了上去。車廂內空無一人,眾人剛待隨機落座,車身一震,火車竟然動了!洛川兄弟帶領大家興奮地齊聲唱起《長征組歌》:「橫斷山、路難行……四渡赤水出奇兵,烏江天險重飛渡……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哪呼嘿!」大家也同時藉機慶祝跳車的當機立斷。
「都去擦把臉,咱這模樣也差了點兒。」洛川兄弟吩咐著。果然,眾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人人都灰頭土臉的,臉上一條條的油泥,就像現在突擊隊員臉上描的迷彩。於是大家輪流去廁所洗臉、方便。一番折騰之後,終於收拾妥當各自落座。隨著列車的行進,車廂中的旅客逐漸多起來了,一直未露面的列車員也以送水為由幾次走過我們身邊。
「壞了,快查票了,大傢伙兒都散散。」洛川兄弟嗅覺敏銳地感到危險就在艱前。還沒容我們反應過來,三位列車員就出現在車廂過道里,他們交替著向旅客逐個查票,並逐步向我們的座位逼近。此時再動也來不及了,事到如今也就只有聽天由命啦。但奇怪的是,他們經過我們時,只是看了看,就繞過我們繼續往後查去。嘿,咱們的運氣咋就這麼好,莫非有天助神佑?眾人正待高興,忽然列車長帶著兩位乘警直奔我們而來,「票、票,大家把票都拿出來。哎,你的票呢?」一位乘警表情嚴肅地伸過手來。「沒票!怎麼著?」我們假裝理直氣壯。「啊?沒票!沒票還這麼拽?補票!」乘警有些惱火。「嘿,新鮮!老子抗戰八年,到哪兒也不花錢。沒錢!」也不知是我們當中的哪位老兄突然冒出句沒頭沒腦的混話,氣氛頓時緊張起來,那乘警聞言正待發作,只聽身後的列車長一聲咳嗽上前接過話來,「你們是幹嗎的?有話好好說,坐車買票,這是國家規定、天經地義的事。看樣子你們也像是學生,咋連這都不懂?」「嘿嘿,車長,您說得不錯,我們過去是學生,可我們現在是農民!」「啊,你們、你們是知青!哪兒的知青?」當確認面前的這批逃票者是在陝北插隊的北京知青時,現場的緊張氣氛明顯緩和下來,嚴肅的列車長態度大變。他努努嘴支走了兩位乘警,隨即挨著我們坐下,並掏出盒「黃金葉」散給大家,這邊有人乖巧地給列車長點上火,原本一觸即發的衝突,隨著從列車長口中吐出的香煙冉冉升起,竟神奇般的化干戈為玉帛了。原來這位列車長的幾個孩子是青島下鄉知青,他也經歷了我們這一代人家長的共同心路歷程,孩子們大致相同的遭遇,使他對我們的境遇充滿了理解與同情。
當列車長得知洛川兄弟幾個都是鐵路子弟並看到我們身上、腿上露出的因水土不服及蛇蚤、蚊蟲叮咬後留下的大小斑痕,他不再說什麼了,只是同情地不住搖頭。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車已快到鄭州,列車長站起身,「坐車都要買票,這是國家規定。不過,」他遲疑了一下,「你們來人跟我去辦張半票,就從這兒算起。到鄭州後,我給你們指條能出站的道兒。然後沿鐵路去鄭州北,到那兒就能搭上去北京的車。哎,孩子們,我能幫你們的也就這些啦,剩下就看你們的運氣了。」這樣的結果,對列車長而言也是在職業操守與同情心這兩難平衡中做出的最好選擇。八個人就買張半票?這當然沒問題!最後列車長回身和我們逐一握手後,並把列車員叫過來吩咐一番,隨後轉身走了。望著他遠去的背影,我心中突然湧起一陣說不出的酸楚。哎,同病相憐啊!
「鄭州,鄭州到了!喂,你、你們跟我來。」列車員招呼著我們,大家下了車,跟著列車員逆著出站的人流疾步前行。突然,列車員站住腳,遙指遠方一處紅磚牆說:「順著鐵路走到那兒,看見了嗎?那牆邊上有個大窟窿,鑽出去就進了鄭鐵局家屬院,再找大門出去就行了。我只能帶你們到這了,我得趕回去上車了,祝你們好運!」還沒容我們和列車員告別,轉瞬間他已跑回並消失在人群中。「夠意思!真是好人啊!」大家由衷地感嘆道。遵照列車員的指點,我們順利地來到了鄭州的大街上。
終於到鄭州了!回家的路已經走了一半,同時我們也到了分手的時刻,我要從鄭州轉道南下信陽去羅山機械院幹校看望母親,而洛川兄弟則準備按照列車長的指點去鄭州北再扒貨車回家。大家依依惜別互道珍重後,就此分開各奔南北。
我一個人又重新回到鄭州火車站,在擁擠不堪的人流中,「現在只剩我一個人啦,可要格外小心,留神別丟東西。」我暗自告誡著自己。抬頭細看時刻表,發現前半夜有班經鄭州去武漢的過路車,到信陽是凌晨五點多。「大半夜的正好沒人查票,買張站台票蹭這班車最合適!」我暗自琢磨著。「得,先找個能吃飯的地兒,混飽肚子再說。」這時,我才突然感到奇餓無比,於是隨意拐進一家掛著「米飯、炒菜」招牌的飯鋪。進去一看菜單,不行,吃這個太貴了。本來錢就不夠,才去扒車,費了多大勁好不容易省下點錢,不能再賠進去了。我咽了咽口水,抗拒住大米飯的誘惑,從這家飯鋪退了出來。得!咱吃面去,吃面最經濟。
鄭州火車站二七紀念塔廣場周邊吃面的小店也是人滿為患,店內的設施環境、烹飪水平、衛生條件等,除要飯的花子比西安站的更多外,其他均與西安站前西八路上的麵館旗鼓相當,如果兩地比賽誰家最差的話,肯定雙方不分伯仲。我隨意吃過兩碗面後,奮力殺出花子們的重圍,回到剛才的街面上。剛出來就被廣場一角的高音喇叭和密密麻麻圍觀的人群所吸引。嗨,那邊在幹嗎?反正時間還早,閑著也無聊,過去看看。走近才知道這是鐵路公安段在為火車上抓到的俗稱「吃大輪」的行竊蟊賊們開批鬥會,一位穿海魂衫留長頭髮的年輕人被人押著推上前台,「這就是李玉和」,一個嚴肅的聲音在廣播喇叭中莊嚴地宣布著。「鐵梅她爹,李玉和咋成了這?」圍觀的群眾竊竊私語、議論紛紛,人群中還不時發出陣陣不嚴肅的嬉笑聲,「咋啦,咋啦?同志們安靜、安靜!哎、哎,他不是《紅燈記》里的李玉和,他是農二師的李玉和!」喇叭里的聲音有些慌亂,隨即台下爆發出一片更大的鬨笑聲。「啥玩意兒嘛,沒勁!」我擠出人群,找個無人的角落坐下,脫下鞋,乘人不注意,看看藏在腳底襪子里的錢還剩多少。這是我最關心的事。還好,還剩十來塊錢,無論南下還是北上,這些錢都夠了,心裡頓時坦然、有底了。
晚上我憑著張站台票如願地混上了開往武漢的過路車。昏暗、悶熱的硬座車廂里人滿為患、座無虛席,衣衫不整的旅客們前俯後仰地睡姿各異,鼾聲此起彼伏連成一片。還有許多人帶著大包小件的行李擁擠在過道里,就連廁所也被人無端霸佔,車廂里空氣混沌、惡劣。隨著「油著、油著,的確良油著」的吃喝聲由遠而近,只見車廂門口一位身著油漬馬哈骯髒廚衣的中年壯漢,一手倒扶著背在背上裝滿餐盒的廚筐,另一隻手攀扶著側邊的行李架,腳蹬著座椅上邊,有驚無險地從坐、卧在走廊、過道中的旅客頭頂穿行掠過,隨即消失在車廂的盡頭,招得眾人抱怨聲、驚叫聲一片,而此時列車員早已龜縮進值班室不見了蹤影。見到這陣勢,我不禁心中竊喜,更聯想起「串聯」時的壯觀景象,那時坐火車都不花錢,所以咱也沒養成花錢買票的習慣。哈哈,太棒啦,這種環境最適合蹭車!隨即我就蹲在過道邊上打盹,實在太累了!
天亮時,火車晚點開進信陽站,趕緊下車透透氣,實在憋得受不了啦!我注意到信陽站出站查票挺嚴,不易矇混過關,且下車人不多,站台更不可久留,只能沿鐵路往外走了。再找找看有沒有類似鄭州站「大窟窿」或鐵絲網破洞之類的地方可鑽?天無絕人之路嘛,終於我發現並從一個鐵絲網破洞中成功地鑽出了車站,來到信陽站前廣場。
信陽是河南省最南端靠近湖北的一座地級市,與鄭州不同的是這裡充滿了南方城市的味道,從風格上來講則更接近武漢。當時信陽地區周邊各縣匯聚了許多中央機關幹校,而機械院幹校也在其中。為方便幹校人員外出往來,幹校多在站前廣場附近設有招待所、接待站,路標醒目而林立。沒費多大勁,我就循路標找到了機械院幹校接待站。自報家門後,站里留守處的人立刻熱情地招呼我吃了飯,並把我託付給一位中年人。飯後恰好有便車去楠桿鋪羅山機械院幹校,我隨後搭車同行。一路上已無心觀風望景,印象中這裡四下平坦全是水稻田,遠處有些不高的小山,這兒肯定是吃大米的!由茅草鋪頂的農舍組成的村莊掩藏在稀疏的樹林里,村前的水塘里飄著浮萍,成群的雞鴨或覓食或鳧水,一派安寧祥和的景象。過往行人的衣著與陝北大補丁摞二補丁的決然不同,看來此地人們一定生活富足,與陝北農村完全兩樣。從而又想起轉幹校和母親在一起的舊事,對,要設法轉到幹校來與親人在一起大約兩個小時後,車到楠桿鋪,有人帶我找到宿舍尋母未果。聽說她正在幫廚,我興沖沖地循著瀰漫在空氣中的飯菜味直奔到食堂,裡面蒸汽升騰地正在開飯。「老單!你兒子來看你啦。」帶我的人高聲喊道。隨著「啊」的一聲,母親瘦小的身軀從食堂門口探出身來,「哎喲,你怎麼來了?」驚詫寫在她的臉上,隨即立刻轉為喜悅,她拉著我左看右看,以至過後久久還不能相信我竟活生生地、從天而降地現身在她的面前。
當她得知我竟是扒火車來到信陽的後,更加吃驚,立刻嚴詞禁止我再做扒車的打算。「這是我們家老三,現在延安插隊。他是專門來看我的。」母親逢人便介紹著。有家人來團聚,除了引來大家的羨慕、稱讚外,不期還招來了幾位打聽陝北情況的家長。我們公社上川某隊女生小萍都在幹校的父母就曾問過我許多當地的情況,據說後來她父母就把她轉來幹校了。轉眼間我在幹校住了三天,要準備回北京了。幹校給我留下的印象首先是伙食好,副食品種繁多,大米飯、白面饃,頓頓管夠,這要在陝北,想都甭想。但白天排隊上工,晚上組織學習,見人還得低眉順目地叫叔叔、阿姨,這太受約束了,不美氣!
一日,拿到預訂好的車票,母親執意請假送我去信陽火車站。一路上她千叮嚀萬囑咐地告誡我:火車不許再扒了,這太危險!沒錢花寫信來要。不許和「壞孩子」學抽煙,沒人管教全學壞了!她要想辦法把我轉到幹校來……「嘿、嘿,幹校這地方兒,好雖好,尤其吃的是真好!可太受管制,不自由,不好玩。還是在陝北和哥們兒混在一起耍,最爽!」我暗自琢磨著,已無心聽母親苦口婆心的諄諄教海,只是「哼哈」應付著。這真是「兒行千里母擔憂,母行千里兒不愁」。只有若干年後,在我娶妻生子成家後,才能體會到「養兒方知父母恩」這句話的含義。
途經信陽北上進京的列車在信陽站停車一分鐘。火車開動時我探身揮手後望,只見母親瘦小的身軀還佇立在站台上,不住地向我揮手。直到站台漸漸退後,消失在遠方。
翌日下午隨著下車的人流,幾經周折的我終又回到了北京——這座陌生而又熟悉的城市。

一出站,我就立刻被那種無處不在且說不清、道不明但又只屬於北京的獨特氣息緊緊地包裹著,熟悉而又親切!望著周圍的人群,我興奮得難以自持,真想沖他們放聲大喊:「北京!我回來啦!」
「大1路來了!」我熟練地一把持住車門,奮力撥開眾人,搶先擠上公交車,只為能早點上車回家。東單、王府井、天安門、西單……逐一經過,看著街道兩邊的自行車潮和過往匆匆的人流,聽著售票員與乘客之間帶兒化音的京腔對話,一切都顯得那麼從容不迫,親切自然。沒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彷彿我從未離開過,就是這喧鬧人群中的一員。恍惚間我已不記得自己是從何處來,又要到何處去,似乎真的從來就沒有離開過這座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而現實中的我,充其量也就是個有親屬在北京的過客。當意識到這些時,又不禁黯然了。
跨進熟悉的樓門,到家了!緊繃的心情終於放鬆了下來。從小看我長大的外婆已有七十多歲高齡,她高興地摸著我的臉看了又看,招呼我洗臉,換衣服。傍晚,盼望時久、已近兩年未曾見過面的父親回家了。分別許久,歷經坎坷的父子終於見面,歡愉之情難以言表。晚飯好吃且豐盛,可口的飯菜由熱變涼,回鍋熱了又熱,我們一直聊到很晚很晚。
那一夜,我睡得格外踏實、特別熟。
摘自朱學夫《陝北往事——我的知青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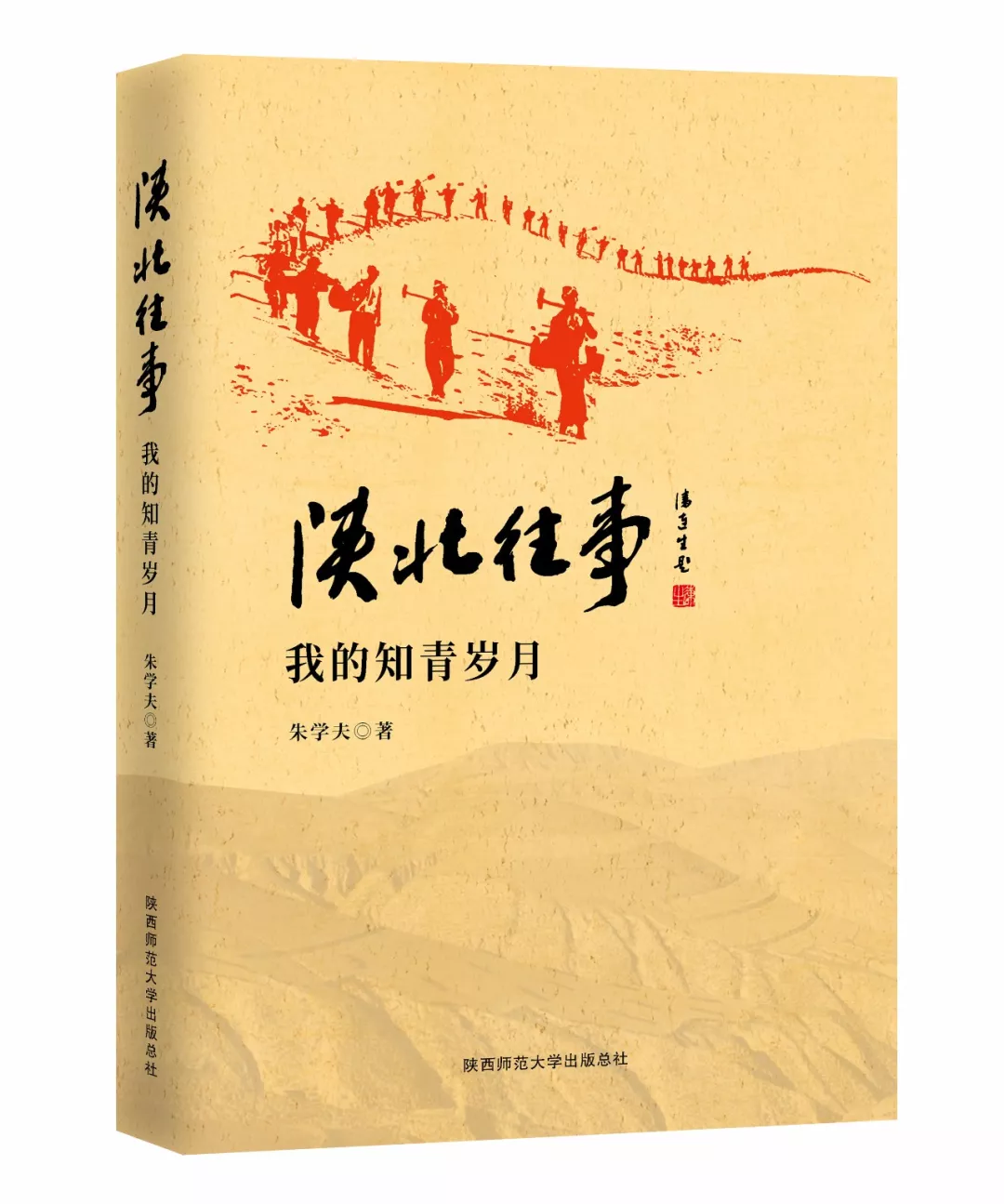


TAG:魯迅讀書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