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紀錄片最高獎《平衡》之美麗的可可西里
原標題:中國紀錄片最高獎《平衡》之美麗的可可西里
點擊上方「 自游烏托邦」可以訂閱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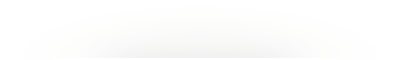
自游烏托邦
kongliming1

訪談背景
訪談背景:10月10日,與成都電視台的彭輝聯繫時,意外獲悉由他拍攝,也是我本次想採訪的關於原西部野氂牛隊、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及可可西里生態環境保護的紀錄片《平衡》,在即將頒獎的第19屆電視金鷹獎中,獲得電視紀錄片的最高獎項---最佳作品獎。 此前,我作為志願者,結束9月份的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工作以後,10月來自《平衡》的震撼--訪《平衡》編導彭輝5日到成都,見到了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的"掌門人"楊欣,恰好在他那裡刻了一套《平衡》的盤。 在保護站曾聽一個7月份的志願者說到《平衡》,評價它是一部"關於痛苦和良心"的片子,一直想看。這次回來以後一放,168分鐘的片長時間,我始終是如哽在胸,內心的震撼無以言述。 10月11日,我用E -MAIL的方式向彭輝提問採訪。當晚12時15分,彭傳回了他的郵件,在看他那些關於扎巴多傑,關於拍攝《平衡》的回憶文字時,我再次被深深打動。 接下來的幾天,我陪不同的朋友在不同的場合又看過三四遍這部片子。每一次看完,大家都久久說不出話來。後來有朋友跟我說:"這些事(關於中國生態環境保護)我們知道得太少了,這是你們媒體的責任。你們炒作這個熱點那個熱點,這樣令人震驚、感動的事,為什麼不好好宣傳?" 國外有媒體曾斷言"中國沒有環保"。但至少,我在9月工作過的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現在是中國民間環保的一個最高標誌,而索南達傑、扎巴多傑更是情願為此一死!類似的組織和全身心投入環保事業的熱血人士,也越來越多。雖然這一切還處於舉步維艱的窘困境況,我卻依然和拍《平衡》的彭輝一樣,相信這個星球人與自然最終的平衡,這種平衡,在中國也絕不會例外。 "許多人是含著熱淚看完全片的" 記者(以下簡稱記):不知道是因為一種怎樣的契機,讓你有拍《平衡》這部片子的想法? 彭輝(以下簡稱彭):我曾經在1996年看到一篇西方報道,稱"中國目前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政府不可能拿出人力、財力從事環境保護",該撰稿人由此得出了"中國目前沒有環保"的荒謬結論,對我觸動很大。 1998年2月,我無意中在由北京日報社出版的《宣傳手冊》(1998年第三期)上看到了題為《可可西里的保護神》的報道,寫的就是盜獵分子的猖狂和"西部野氂牛隊"的事迹。經報請台領導同意,半個月後,我開始了長達三年多的艱苦創作,經歷了一次次生與死的考驗,為西部工委窘迫的現狀感到震驚,更經歷了對盜獵者的憤怒和對兩任工委書記先後去世的陣痛! 記:為什麼會取名《平衡》呢?我的一個朋友認為這個片子有一個高潮點,就是最後扎巴多傑發脾氣那個鏡頭,除此都拍得很冷靜,他認為那個鏡頭給他留下了很震撼的印象。《平衡》的名字是不是直接從那裡而來? 彭:這個問題應該把它放在整個創作背景中來回答。 (1)我眼裡的"西部野氂牛隊" 與國內外的一些媒體報道不一樣,我在《平衡》里沒有片面地把"西部野氂牛隊"塑造成完美的英雄,畢竟我與他們相處了三年,畢竟我是一名記者,是一名以事實說話的紀錄片工作者。許多人把"西部野氂牛隊"神話化了,甚至成了"西部工作委員會"的代名詞。事實上,"西部工作委員會"才是這個環保組織的正式名稱,是經中共青海玉樹州委批准成立的基層組織。"西部野氂牛隊"只是該委員會的一個有民間特色的稱號。 由於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落後,隊員文化素質偏低,加上地域相對封閉等客觀因素,使巡邏隊在頑強、勇敢、敬業的同時,也缺乏一定的科學管理,讓我感覺他們堅強剛毅、有激情,又不太規範。 在《平衡》里,我採用了"真實電影"的創作手法,不用一句解說詞,把我捕捉到的情節儘可能地保持原貌,客觀地呈現給觀眾,讓觀眾看到這支名揚國內外的武裝巡邏隊的真實。 (2)我眼裡的兩任書記 第一任書記索南達傑被稱為"青藏高原的環保戰士、可可西里野生動物的守護者"。第二任書記扎巴多傑是《平衡》的主要人物線索,也是我從事記者工作15年來最為敬佩的縣級幹部之一。 在我看來,扎巴多傑的人格魅力在於他能與隊員同甘共苦、不分彼此的同時,從不隱瞞自己的不足,乃至錯誤。更為可貴的是,他一直在自覺不自覺地糾正自己的一些不規範的行為,這一點在有些幹部的身上是難以做到的。在《平衡》中,扎巴多傑面對觀眾說出了一些實際上很不利於他自己形象的大實話,這是他做人的坦蕩之處,這也是我為了保持《平衡》的客觀性所作出的一點努力。 在1998年8月的一次巡邏中,我們的採訪車和巡邏隊的所有車輛全部深陷於可可西里著名的"鬼門關"。在那三天兩夜裡,我們和所有隊員一樣只吃了兩根冰涼發硬的火腿腸;晚上和衣坐在車裡,車外是零下5度的氣溫和肆虐的風雪!許多隊員的耳朵凍得直流水。每天一早,渴了一夜的扎巴多傑一走出車門就趴在稀泥地上,埋頭去喝車轍里積存的泥水,其他隊員也紛紛效仿吸起泥水來…… 還有一次,在追捕盜獵分子十幾天後,巡邏隊已沒有任何糧食,幾名隊員出現嚴重的不良反應,他們只好去撿盜獵分子逃匿時吃剩扔掉的糌粑和煙頭! 這就是可可西里的夏季!這就是扎巴多傑和他的"西部野氂牛隊 我始終不能忘記在一次巡邏過程中,扎巴多傑坐在雪地上,一支衝鋒槍靠在他的肩膀上,對我說:"我就不信中國沒有環保,別人不做,我來做!" 1998年10月,也就是扎巴多傑在北京尋求活動經費期間,香港"地球之友"總幹事吳方笑薇到"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時,幾位堅守在那裡的野氂牛隊員說:"已經斷糧好幾天了,沒有油,沒有肉,每天只能吃糌粑度日。"環保志願者楊欣把帶去的罐頭送給又黑又瘦的隊員時,他也不知道,隊員們已經整整10個月沒有領到一分錢工資了。 也就是在這10個月里,發生了個別隊員私賣羚羊皮的事件。 作為一部客觀記錄歷史的作品,《平衡》沒有使用一句有可能產生主觀導向作用的解說詞。讓事實說話,讓歷史說話,是我創作《平衡》的基本原則。 個別媒體在"撤消西部工委"(2000年12月底)問題上大做文章,把"撤消"當成了貶義詞大肆渲染。"撤消"是機構調整工作中常用的中性術語,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他(她)應該懂得這個常識。西部工委是按照國家統一部署,為解決可可西里長期多頭管理問題,經中共玉樹州委批准撤消的。西部工委八年的功績沒有,也不可能因必要的機構調整而被忽略,甚至抹殺,它已成為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永遠地停留在人們的記憶當中。 2000年11月,《平衡》應邀參加上海國際電視節,分別在紀錄片研討會上和復旦大學放映了兩場,現場觀眾在觀看過程中數次報以熱烈的掌聲,許多人是含著熱淚看完全片的。 "平衡"的片名是我經過一段時間的採訪創作之後的思考結果,是在1998年5月給台里做書面彙報時取的名字;扎巴多傑是同年的10月1日晚在北京的一家招待所里說出的"平衡"兩個字。一個月後,他在家裡死亡。這中間有什麼聯繫,我不敢想。 也許,《平衡》記錄的就是人們尋找生態平衡,尋找心態平衡,尋找人文平衡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觸動了一些敏感的神經和經歷正視現實的陣痛。但我相信,陣痛總會過去,現實必須正視,歷史將證明一切。 "就讓他的死成為永遠的謎吧" 記:片子拍了當時野氂牛隊巡山的很多細節,你是一直在連續不斷地跟拍,還是只有選擇性地進去可可西里幾次? 彭:可可西里是中國著名的"生命禁區"。那裡的自然條件決定了我們不可能長時間地呆在那兒採訪。 你去過保護站,知道那裡的氣候。但可可西里腹地的氣候與保護站周圍的氣候完全是兩回事,那裡更加惡劣! 我們的設備很簡陋,就是一台攝像機、一個腳架,連野外拍攝最起碼的防風防雨設備都沒有,一遇到風雪,我們就靠自己的身子和幾把雨傘來為器材遮擋。所以設備經常是不能正常工作。在去年的一次巡邏中,因為氣溫太低,還損壞了一台攝像機,只好中途返回成都。 記:扎巴多傑是1998年11月8日離世的,你跟拍他一直到了10月,最後那個鏡頭,他的情緒很激憤,甚至說到了"連死都不怕",這讓我感覺他當時是不是有什麼預感? 彭: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謎。我想,現在再去尋找扎巴多傑的死因已經不那麼重要了。重要的是,扎巴多傑的死能讓我們理解到什麼?感悟到什麼?如果他的死能夠喚醒更多的人的環保意識,能夠揭示出我們在體制上的一些弊端,不要再讓它成為我們工作的絆腳石,甚至帶來一些無謂的犧牲的話,那麼,就讓他的死成為永遠的謎吧。 記:你聽到扎巴多傑死亡的消息,當時有什麼感覺?你一直在拍他,關係應該很親密,你肯定沒有想到所拍的對象會以突然的、非正常死亡的方式為這部紀錄片畫上句號。這讓人心裡感到特別的震駭。 彭:1998年9月,因嚴重缺乏經費,已無法維持正常巡邏工作的扎巴多傑來到北京尋求幫助。9月24日晚上,扎巴多傑結束了一天的演講後,和我準備一起吃晚飯。我們聽說當天中央電視台"電影頻道"要播出故事片《傑桑·索南達傑》(珠影廠拍攝),由於我們下榻的招待所不能收看電影頻道的節目,他決定找一家能看到電影頻道的餐館吃飯。 在景山公園西門附近找到了一家能收到電影頻道的小飯館。當黑白屏幕上的《傑桑·索南達傑》播放到一半的時候,扎巴多傑已淚流滿面,他哭著對我說:"只要有人理解,我就是死在可可西里也心甘情願。" 讓我久久無法相信的是,扎巴多傑最終沒能死在可可西里。 11月8日晚,一顆充滿疑點的子彈擊穿了扎巴多傑46歲的生命!擊碎了西部野氂牛隊的希望! 我是11月10日下午得到扎巴多傑去世的消息的。當時我在機房裡做我的另一個紀錄片《背簍電影院》。一位我和扎巴多傑都熟悉的朋友打來電話,說扎巴多傑"走了",我還責怪地說:"怎麼會呢?他不是跟我約好了11月20日才一起去北京的嗎?怎麼就先走了?"但僅僅一分鐘,我突然意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進一步追問之後,我呆了。我立即掛了電話,重新打到西部工委證實,工委的副書記梁銀權哽咽地證實扎巴多傑已經死亡。在他還沒正面回答我的問題時,我的眼淚已經默默地流到了嘴角…… 我幾乎是失去理智地直接把電腦的電源開關關掉,跑回辦公室,用E -MAIL與中央台的幾個朋友聯繫,想從他們那裡得到更多的消息。眼淚一直無聲地流淌著,同事們不停地點燃香煙遞給我,誰也沒有說話。 之後,我買了最早的航班趕到西寧,當我坐了幾天的長途汽車趕到扎巴多傑家時,他剛剛天葬。那個和我在冰天雪地生死與共的康巴漢子永遠地從我的視線里消失了!消失得是那樣的快,連讓我最後看他一眼的機會也沒給我! 聽扎巴多傑的家裡人說,扎巴多傑天葬那天來了很多的老鷹。他們認為,老鷹來得越多,逝者就越早進入天堂,越早脫離塵世的痛苦。 扎巴多傑終於帶著他的夢隨鷹背而去了。 扎巴多傑是悲壯的,野氂牛隊是悲壯的。 "它(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更大的價值是表明了一種態度,一種中國人在環境保護上的最感性、最原始、也是最文明的態度。" 記::我在片中看到了一些我認識的人,像謝周、扎多等,感到很親切。在保護站的時候,我們偶爾也會提到野氂牛隊的事,他們的神情都顯出極大的落寞,比如謝周,我覺得他已經變得很憂鬱。不知道你個人對野氂牛隊總的感覺是怎樣的?對它最終被解散的結局怎麼看?對可可西里保護區的整個前景又怎麼看? 彭:關於對巡邏隊的感覺,我想這個問題已經在前面作了部分回答。至於對可可西里的前景的看法,我會在今後的《平衡續集》中回答,我不會在這裡做任何推斷和猜測(無非就是說些"我相信、我希望"之類的大道理),紀錄片是用事實說話的。 記::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在片子里也佔了比較大的比例。對這個民間性質的保護站,你的評價如何?你和楊欣(索南達傑保護站的發起和組織者)都是成都人,可以談談你眼中的楊欣及他目前從事的事業嗎? 彭:中國有很多事情其實辦起來並不複雜,關鍵是你願不願意去做。 建立保護站的意義,我想還不在於僅僅是為某個巡邏隊提供了活動基地。它更大的價值是表明了一種態度,一種中國人在環境保護上的最感性、最原始、也是最文明的態度。這種態度是需要勇氣和能力才能表達出來的,而楊欣就具備了這兩點。因此,他把這種態度樹立在了可可西里。 有人說楊欣在環保事業上存在功利心,我不做評價,因為我不了解他這一點。但是,我認為,我們更應該把視覺的注意力放在楊欣在中國的環保事業里所做努力的意義上。他做的事並不算驚天動地,有很多人也許可以做,甚至做得更好。但是,楊欣已經做了。 記:你個人覺得環保在中國所受到的關注程度怎麼樣?從政府到社會、民間都可以談。而且對這個問題的前景,你感到樂觀嗎?為什麼?片子里扎巴多傑訪談部分,他眼裡始終都是有眼淚的感覺,楊欣在海口演講甚至哭了,他在一個律師事務所賣20本書的鏡頭,讓人心裡也很不是滋味。 彭:可以肯定地說,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在世界的地位的進一步提高,中國政府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也會隨之提高。畢竟,環境保護的力度最終是要體現一個國家的經濟水平和文明程度的。 扎巴多傑,楊欣,西部工委,保護區管理局,還有許許多多致力於環保的人們,他們現在的一切努力正在使我們的國家一步一步走向文明,儘管這個過程有辛酸的淚水。 記:這部片子從拍攝到後期製作總共用了多長時間?順利嗎?你所在的電視台是不是很支持? 彭:《平衡》從前期策劃、拍攝,到後期完成,用了三年多時間,而且現在我仍然在繼續關注可可西里,繼續關注《平衡》的人物命運。 今年5月,我又去了格爾木,記錄了幾名涉案隊員,以及可可西里環境保護的現狀,特別採訪了目前主要負責可可西里自然環境管理的"保護區管理局"。我準備在有條件的基礎上,把《平衡》一直拍下去,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紀錄片。 我是從1994年開始創作紀錄片的,以前一直在搞專題片。台里對我一直非常支持,我報的選題從來還沒有被"槍斃"過,申請的經費也從來沒有被"剋扣"過。當然,我是用每一個片子的質量取得了台里的充分信任。總的來說,我的創作環境是相對寬鬆的,這也是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考慮"跳槽"的主要原因(曾經有幾個大台找我接洽過,希望去他們那兒工作)。 記:片子結束時,我終於看到了你們工作的一些鏡頭,像打著傘替攝像機擋風雪,像你在清水河(是那裡嗎?)洗臉時冷得跳起來,心裡特別有感觸。那一定是很艱辛的一段日子。謝周唱歌敬酒為你們送行,那也是很珍貴的一種感情。拍了這個片子以後,你自己的心情怎樣?對你的生活有什麼重要影響嗎?會不會有些什麼東西是與以前不同了呢? 彭:實在有點累了,前幾天得了急性腸炎,現在還有點發燒。我會給你寄些VCD,其中有張是《記錄平衡》,你看看,也許能回答你這個問題。 記:我不太了解你的工作背景,可以介紹一下嗎?比如現在主要做什麼,還有其他什麼作品等等。 彭:這個問題在"彭輝簡歷"中有。 記:我跟一些朋友一起看《平衡》,我們都覺得這部片子拍攝的理念很獨特。特別地內斂,不張揚,質樸。沒有一點刻意煽情的東西,沒有一句解說詞,除了謝周唱的歌,也沒有其他過雜的音樂背景,而且你是特意將自己隱在這個場景的背後。這都是我們很直接的感性認識。你自己可以談談你對這個問題的一些思考嗎?有沒有從金鷹獎那方面傳遞過來的評價信息? 彭:我曾經說過一句話,也是我創作紀錄片的一個始終堅持的基本觀點:"我試圖想把紀錄片的創作看成是對生活的複製"。紀錄片工作者就是有責任把你看到的最原生態的東西展示給觀眾,否則就不叫紀錄片。這種"原生態"是最能體現紀錄片的真實性的。 那麼,體現這種"原生態"的創作方式有很多種,但對《平衡》而言,我至今仍然認為只有一種,那就是我現在採取的"不要解說詞,由主人公扎巴多傑主述"的形式。因為這個巡邏隊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它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決定了任何一個聲音來做解說都無法達到扎巴多傑自己講述的震撼力。由於扎巴多傑的人格魅力,他在片中毫無掩飾地講述了巡邏隊的功績和缺陷,賦予了《平衡》"真實"的生命。我很滿意我堅持了這種創作形式。 我沒有從金鷹獎方面得到任何評價的信息,甚至到現在我也沒有收到獲獎的正式通知。 記:《平衡》在國內播過嗎?它是不是在匈牙利獲過獎?這次獲金鷹獎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 彭:《平衡》首先在成都電視台播過,是播的全篇,168分鐘。四川台和中央台也應該播過,他們主動找到我要的帶子。 在今年4月舉辦的第十二屆匈牙利國際藝術電影節上,《平衡》和我的另一部紀錄片《空山》都獲得最佳紀錄片提名(當時有30多個國家的1400多部影片參賽,有15部作品獲得提名),最終是《空山》贏得最高獎---評委會大獎。頒獎後,電影節主席告訴我:"《平衡》和《空山》都很好,《平衡》很震撼,但較之《空山》來說比較難理解,《空山》更容易看懂。"畢竟是外國人,他們對我們國家的一些機構不太理解,而這正是《平衡》所要表現的。 金鷹獎是我國電視藝術的最高獎。我曾經三次獲提名,但最終無緣"金鷹"。雖然這幾年頻頻在國際上,以及在國內紀錄片的專業評比上獲獎,但金鷹獎一直是個空白。 實話實說,本來今年我不想參加金鷹獎的評選,因為金鷹獎需要觀眾投票這個特殊性,使我早已失去了捧杯的信心。畢竟,關注紀錄片的觀眾並不多,喜歡看的,又看上你的片子的,然後還要上街掏錢買選票,還要為你跑趟郵局的觀眾更是不會多。但我還是按要求,習慣性地報了名。 獲獎的消息還是成都一個不認識的文化記者打電話告訴我的,他說組委會在北京剛剛召開了發布會,公布了全部的獲獎名單,《平衡》不僅獲了獎,還是紀錄片的第一名,最佳長篇紀錄片。這消息很好,但也很突然。我問他:金鷹獎不是應該在頒獎晚會上公布獲獎名單嗎?怎麼提前公布了?他說今年改了。我想應該證實一下,就按照那個記者提供的方式在網上查,結果我就樂了。不光是我得獎的問題,關鍵是《平衡》得了獎。從拍攝,到製作,再到輿論,到謠言,三年多時間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不容易啊!巡邏隊不容易,《平衡》不容易,得獎不容易,得金鷹獎就更不容易!
﹁
自游烏托邦
﹂
長按識別二維碼關注我們!
您看此文用 · 秒,轉發只需1秒呦~




點擊「閱讀原文」


※中國第一所教會合辦大學
※全世界只有中國的醫院標誌是十字架?為什麼?
TAG:自由烏托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