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前活躍在世界舞台上的無政府主義和民族主義力量,是如何相遇並互動的?
原標題:一戰前活躍在世界舞台上的無政府主義和民族主義力量,是如何相遇並互動的?

編者按:19世紀最後幾十年,萬國郵政聯盟的成立,電報、海底電纜的發展使信息在全球範圍內的快速流通成為可能;與此同時,蒸汽船的出現及日益細密的鐵路網路聯結起了分布在世界版圖上的不同國家和大洲。在這些條件的促成下,全球經濟文化的連接日漸緊密起來,現代意義上「早期全球化」由此拉開帷幕。
也是在這一時期,無政府主義和民族主義力量借全球化創造的機會,活躍於世界舞台之上。1895年至1896年,古巴和菲律賓作為西班牙帝國最後僅存的兩處重要殖民地,幾乎同時發生了民族主義起義。其間,兩地的革命者不僅互通有無,而且還有著重要的民間聯繫,在一定程度上協調各自的行動;與此同時,法國、西班牙、義大利、比利時和英國的無政府主義者也成為了他們當時最可靠的盟友。當代著名理論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將上述兩場反殖民抗爭稱為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的全球性協作」。
它們也成為了《全球化時代》一書論述的入口。在這本新書中,安德森選擇從雖處於世界體系邊緣、但曾在當時扮演了世界性的角色的菲律賓下筆,逐漸向歐洲、美洲和亞洲發散,試圖描繪世界各地的激進民族主義之間的無政府主義重力。無政府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如何在早期全球化時代相遇並進行互動的?在安德森的歷史書寫和分析里,我們或能找到這一答案,又或能觀照到我們自身所處的這個時代。
今天的推送節選自該書的導言部分。它為我們淺略描摹了一幅一戰前的政治和文化圖景,也為我們進入本書的核心議題做出了重要的鋪墊。
一戰前活躍在世界舞台上的無政府主義和民族主義力量,是如何相遇並互動的?
文/本尼德克特·安德森
節選自《全球化時代:無政府主義者與反殖民想像》
仰望熱帶旱季沒有月亮的夜空,可以看到閃耀的群星。星星固定不動,連接它們的只有人的想像,還有可見的黑暗。這場景極具靜謐之美,所以需要動番腦筋才能想到,群星其實永遠在狂亂地運動著;它們無可逃避地處在各種重力場當中,在中間積極運動,也處處受無形力量的驅使。比較研究的方法便帶有這種占星術般的優雅,比如我就曾藉此將「日本」與「匈牙利」、「委內瑞拉」與「美國」、「印度尼西亞」與「瑞士」的民族主義並列而論。每一個對象都在發出各自穩定而獨有的光彩。
當夜空降臨革命中的海地,此時的夏爾·勒克萊克將軍正統率著黃熱病流行的波蘭軍隊。他們是拿破崙派來重建奴隸制度的。就在不遠處,他們聽到敵軍正在歌唱《馬賽曲》和《一切都會好!》(?a ira!)。這簡直是種羞辱,拒絕執行屠殺黑人俘虜的命令是他們做出的回應。蘇格蘭啟蒙運動對塑造美國反殖民起義有決定性意義。西班牙裔美洲民族主義獨立運動與自由主義、共和主義的普世主義浪潮密不可分。浪漫主義、民主、唯心主義、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乃至後來出現的法西斯主義,無不被認為擁有向全球伸展、連接起各個民族的特徵。民族主義是其中化合價最高的元素,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時間與其他各個元素相結合。

克魯泡特金
本書是一次政治天文學的試驗,也許梅爾維爾(Melville)會用這個詞。它試圖描繪世界各地的激進民族主義之間的無政府主義重力。伴隨著第一國際的解散以及1883年馬克思的逝世,無政府主義這個元素以它一向以來的多樣形式,主導了擁有國際主義自我意識的激進左派。無政府主義在年輕一代產生了一位富有說服力的哲學家克魯泡特金(年齡比馬克思小22歲),還有一位有趣而極具魅力的活躍分子兼領袖馬拉泰斯塔(Malatesta,年齡比恩格斯小33歲),令馬克思主義主流無可企及。但還不止於此。縱然無政府主義常常借用馬克思高聳的思想大廈,但在一個真正的工業無產階級主要局限於歐洲北部的時代,無政府主義運動並沒有輕視農民和農業勞動者。以個人自由的名義,它向「布爾喬亞」作家和藝術家開放,這在當時體制化的馬克思主義當中是沒有的。就像它敵視帝國主義那樣,它對「卑鄙的」「非歷史的」民族主義(包括殖民世界的那些)也沒有理論偏見。無政府主義者還更加迅速地利用了那個時代規模空前的跨洋遷移。馬拉泰斯塔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待過四年—對於從未出過西歐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這是難以想像的。五一勞動節是為了紀念1887年在美國被處決的無政府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移民。
本書關注的時期是19世紀最後幾十年,為此還有其他幾個理由。新世界的最後一次民族主義起義(古巴,1895年)和亞洲的第一次民族主義起義(菲律賓群島,1896年)幾乎同時發生,這並非偶然。古巴和菲律賓同是著名的西班牙全球帝國最後僅存的重要殖民地。兩地的原住民即古巴人(以及波多黎各人和多米尼加人)和菲律賓人不僅互通有無,而且還有著重要的民間聯繫,在一定程度上協調各自的行動——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這種全球性的協作。最終,起義相繼在幾年內遭到行將成為世界霸主的美國的同等殘酷的鎮壓。不過,奧連特(Oriente)和甲米地(Cavite)破碎的山村之間沒有直接的協作,而是通過「代表」從中穿針引線;尤其重要的是巴黎的代表,其次是香港、倫敦和紐約的代表。中國民族主義者在報紙上讀到這些消息,熱切地關注古巴和菲律賓的消息—還有菲律賓人也曾學習過的反對英帝國主義的布爾民族主義鬥爭—從中學習如何「干」革命、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帝國主義。菲律賓人和古巴人在不同程度上發現,他們最可靠的盟友是法國、西班牙、義大利、比利時和英國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們這麼做各有各的理由,常常並非出於民族主義。
這些協作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19世紀最後20年見證了——我們不妨稱之為——「早期全球化」的開端。電報發明以後迅速得到許多改進,跨洋海底電纜也鋪設完畢。全球的城市人民很快就對電報習以為常。1903年,西奧多·羅斯福向自己拍發了一封環球電報,在九分鐘之後收到。1876年萬國郵政聯盟成立,大大加速了信件、雜誌、報紙、照片和書籍在全球的可靠投遞。安全、迅捷而廉價的蒸汽船使國家與國家、帝國與帝國、大洲與大洲之間有了大規模移民的可能,史無前例。日益細密的鐵路網路在國家和殖民地邊界內運送數以百萬計的人和商品,偏遠的內陸得以相互連接,並通達港口和首都。
在1815—1894年這80年間,世界大體處於保守的和平之中。美洲以外,幾乎所有國家都是專制或者立憲的君主制。三場最漫長、最血腥的戰爭發生在世界體系的邊緣——中國和美國的內戰,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亞戰爭,以及60年代巴拉圭與其強鄰之間的可怕鬥爭。俾斯麥壓倒性地擊敗了奧匈帝國和法國,迅如閃電,沒給自己帶來多少人員損失。歐洲在工業、金融、科技和財政資源上的巨大優勢,使得帝國主義在亞洲、非洲和大洋洲無人能擋,只有印度的叛亂是特例。資本也迅速地、頗為自由地穿越現存的國家和帝國邊界。

俾斯曼
但是,19世紀80年代以降,人們已經開始感受到初步的震顫,它預兆著日後我們有著各自記憶的那場地震——第一次世界大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1881年被投擲炸彈的激進分子暗殺,這些人稱自己為「人民意志黨」(The People』s Will);在接下來的25年間,又有一位法國總統、一位義大利國王、一位奧地利皇后和一位王儲、一位葡萄牙國王和他的繼承人、一位西班牙總理、兩位美國總統、一位希臘國王、一位塞爾維亞國王,以及俄國、愛爾蘭和日本的勢力強大的保守派政治家被殺。當然,暗殺失敗的次數要比這多得多。無政府主義者實行了最早也最引人注目的暗殺活動,但民族主義者不久也緊隨其後。多數事件導致的直接後果是各國頒布大批嚴酷的「反恐怖主義」立法,實行就地處決,(公共和秘密的)警察還有軍隊採用刑訊的做法也日趨平常。但那些暗殺者——有些可謂是早期的自殺式爆炸襲擊者——認為自己此舉是在通過新聞機構、報紙、宗教進步主義者、工人階級還有農民組織等,向全世界的觀眾表演。
遲至1880年,帝國主義競爭仍主要發生在英國、法國和俄國之間,而後進國家如德國(在非洲、東北亞和大洋洲)、美國(在太平洋對岸和加勒比海內部)、義大利(在非洲)和日本(在東亞),正日益使帝國主義的競爭加劇。抵抗運動同樣正展現出更現代、更有力的面貌。19世紀90年代,西班牙不得不派出有史以來最大的軍力,穿越大西洋,以圖粉碎古巴的馬蒂(Martí)起義。在菲律賓群島,西班牙頂住了一場民族主義起義,但未能將其擊敗。在南非,布爾起義震動了大英帝國老邁的身軀。
本書的主角們正是遊走於這樣一個舞台之上。也許這樣說會更生動一些:讀者將會在阿根廷、新澤西、法國和巴斯克人故鄉碰到義大利人,在海地、美國、法國和菲律賓碰到波多黎各人和古巴人,在古巴、法國、巴西和菲律賓碰到西班牙人,在巴黎碰到俄國人,在比利時、奧地利、日本、法國、英國和中國香港碰到菲律賓人,在墨西哥、舊金山和馬尼拉碰到日本人;在倫敦和大洋洲碰到德國人,在菲律賓和日本碰到中國人;在阿根廷、西班牙和衣索比亞碰到法國人,等等。
從原理上講,選取任何一個地方都能研究這個廣闊的地下莖網路——研究俄國最後肯定會研究到古巴,研究比利時會想到衣索比亞,研究波多黎各也不能忽視中國。但本書這項特別的研究之所以從菲律賓開始,有兩個簡單的理由。首先,我和菲律賓關係很深,20年來斷斷續續對它有所研究。其次,在19世紀90年代,菲律賓雖然身處世界體系的邊緣,但它一度短暫地扮演過世界性的角色。還有一個次要的理由,就是我能夠接觸到菲律賓的材料。研究所關注的三位人物(小說家何塞·黎薩爾(José Rizal),人類學家、記者伊薩貝洛·德·洛斯·雷耶斯(Isabelo de los Reyes),以及協調組織者馬里亞諾·龐塞(Mariano Ponce)),都出生在19世紀60年代初,彼此年齡相差不過三四歲,生活在複印、傳真和網路尚未降臨的宗教時代。他們著述頗豐—書信、小冊子、文章、學術研究和小說。他們用的是落筆後無法修改的鋼筆和墨水,寫在被認為保存壽命近乎永久的紙上。(美國檔案館至今仍拒絕接受任何複印材料,因為20年後它就會變得模糊不清;也不接受電子格式的材料,因為技術創新的生猛步伐,電子材料甚至很快就會無法讀取或者讀取成本非常之高。)

何塞·黎薩爾
儘管如此,一項走過里約熱內盧、橫濱、根特、巴塞羅那、倫敦、哈勒爾、巴黎、香港、斯摩棱斯克、芝加哥、卡的斯、太子港、坦帕、那不勒斯、馬尼拉、利托梅日采、西礁島和新加坡的研究,再怎麼膚淺,也需要有自己的組合敘述風格。這種風格有兩個核心要素:第二個要素是(歷史學意義上的)愛森斯坦的蒙太奇,而第一個要素是查爾斯·狄更斯和尤金·蘇(Eugène Sue)所創作的連載小說(roman-feuilleton)。因此,讀者需要想像自己在欣賞一部黑白電影,或是閱讀一部未竟的小說,它的結局超出了這位疲憊小說家的視野。
做一名好讀者還有一項負擔。在19世紀晚期,還沒有什麼醜陋的、貶值的「國際語言」。菲律賓人跟奧地利人寫信用的是德語,跟日本人用的是英語,相互之間用的是法語、西班牙語或者塔加洛語(Tagalog),字裡行間透露出最後那種國際語言——典雅的拉丁語的人文熏陶。他們當中有人懂點俄語、希臘語、義大利語、日語和漢語。將電報傳遍全球也許只是幾分鐘的事,但真正的交流需要有掌握多語種之人真誠、堅實的國際主義。菲律賓人的領袖在這樣一個巴別塔式的世界如魚得水。政敵的語言同時也是他們私人之間所講的語言,在菲律賓卻只有不到5%的人能夠聽懂。塔加洛語是馬尼拉及其周邊的土著語言,大部分菲律賓人都聽不懂,對於國際交流無論如何都沒有用處。許多操其他地方語言(尤其是宿霧語和伊洛卡諾語)的人更傾向於說西班牙語,即便在菲律賓這種語言是精英或者菲奸身份的明顯標記。為了讓讀者最生動地體會到這個已經消失的多語世界,本研究引用的都是不同語言的原文,這些人就是用不同的語言相互交流並與非菲律賓人交流的。(除特別指出外,本書中所有的翻譯都是我所做。)
註:題圖為處決無政府主義者,巴塞羅那。
▼

《全球化時代》
副書名:無政府主義者與反殖民想像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
董子云 譯
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
ISBN : 978-7-100-16664-5
▼
19世紀晚期,電報、萬國郵政聯盟、鐵路與蒸汽船使得跨國連接成為可能,早期全球化已然開端。人口遷移與觀念傳播同時進行,無政府主義與民族主義相遇,其信奉者實施了目標和次數都引人注目的暗殺行動,引發了早期的「反恐怖主義」立法;古巴與菲律賓作為西班牙帝國僅存的兩處重要殖民地,幾乎同時爆發民族主義起義,其間革命者互通有無、協調行動,成為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全球性合作。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從菲律賓下筆,逐漸向歐洲、美洲和亞洲發散,聚焦於以菲律賓國父、小說家何塞·黎薩爾為代表的一批民族主義者,再現了「一戰」前的世界政治與文化圖景。在此基礎上,他試圖闡明早期全球化時代無政府主義如何影響了民族主義,而全球組織網路又如何塑造了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運動。
購買《全球化時代:無政府主義者與反殖民想像》
編輯 | 咬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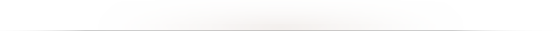


TAG:三輝圖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