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東如何形成?專訪英國史學家詹姆斯?巴爾
原標題:現代中東如何形成?專訪英國史學家詹姆斯?巴爾
我出生於80年代末。有一個話題,即便我和同齡人從來沒有特別關注和深入挖掘過,也依然通過將近二十多年的媒體新聞耳熟能詳了:無休止的中東戰亂。巴以衝突、「土地換和平」、自殺炸彈、聖戰、真主黨、巴解組織、基地組織、9·
11
事件、恐怖襲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阿拉法特、沙龍、穆巴拉克、卡扎菲、薩達姆、阿薩德、埃爾多安、伊斯蘭國,這些名字和名詞是我們這代人非常熟悉的。中東為什麼這麼亂?宗教、民族、政治、鐵腕強人、獨裁、石油,這些都是一些粗略的答案。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上面涉及的幾乎所有地區都在奧斯曼帝國統治下,儘管帝國的統治在不同地區的程度和效力差異很大。但當時的大部分阿拉伯人都至少在名義上接受奧斯曼蘇丹(同時是伊斯蘭世界的哈里發)的統治。而幾年之後,戰爭結束,奧斯曼帝國分崩離析,本來(至少表面上)大一統的格局就變成了無數個碎片。向心力一瞬間消失了。
英法這兩個殖民主義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取代奧斯曼帝國,成為中東霸主,並瓜分了這片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地區。法國獲得敘利亞和黎巴嫩。英國控制巴勒斯坦地區和美索不達米亞。一戰期間為了拉攏阿拉伯人起來反抗奧斯曼帝國,英國人向麥加的哈希姆(聖裔,即先知穆罕默德的後代)家族發誓許願,將來幫助他們建立獨立的阿拉伯國家。同時,為了維持與法國的盟友關係,英國又與法國達成秘密協定,瓜分中東。
同時,為了拉攏猶太人,英國又承諾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的民族家園。英國的三個承諾是互相抵觸和矛盾的。為了戰爭勝利慌不擇路地胡亂許願,在戰後就釀成了嚴重後果。哈希姆家族的夢想破滅,沒能建立起統一的大阿拉伯國家。部分是出於內疚,英國人(在當時的殖民事務大臣丘吉爾領導下)扶植哈希姆家族的兩個兒子分別成為約旦國王和伊拉克國王。英國在一戰時期的另一個盟友沙特家族最終在阿拉伯半島稱霸,驅逐哈希姆家族,建立了現代的沙烏地阿拉伯。二戰期間,英國和法國牢牢控制中東,讓德國人煽動阿拉伯人起來反抗英法殖民統治的夢想沒有實現。
等到二戰結束後,在歐洲經歷了地獄的猶太人紛紛湧向巴勒斯坦地區。而英國政府害怕猶太人與當地阿拉伯人之間爆發衝突,遏制猶太人的移民,這引起了猶太人的憤怒,他們不惜以恐怖主義手段來對付曾經對猶太人抱有善意的英國人。戰後元氣大傷的英國無力控制巴勒斯坦局勢,最後單方面撤離。以色列建國,驅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與多個阿拉伯
國家爆發多次戰爭,衝突至今。而曾經的英國殖民地埃及獲得獨立,納賽爾、薩達特和穆巴拉克等幾位世俗化獨裁者連續統治。在伊拉克,軍人政變推翻了君主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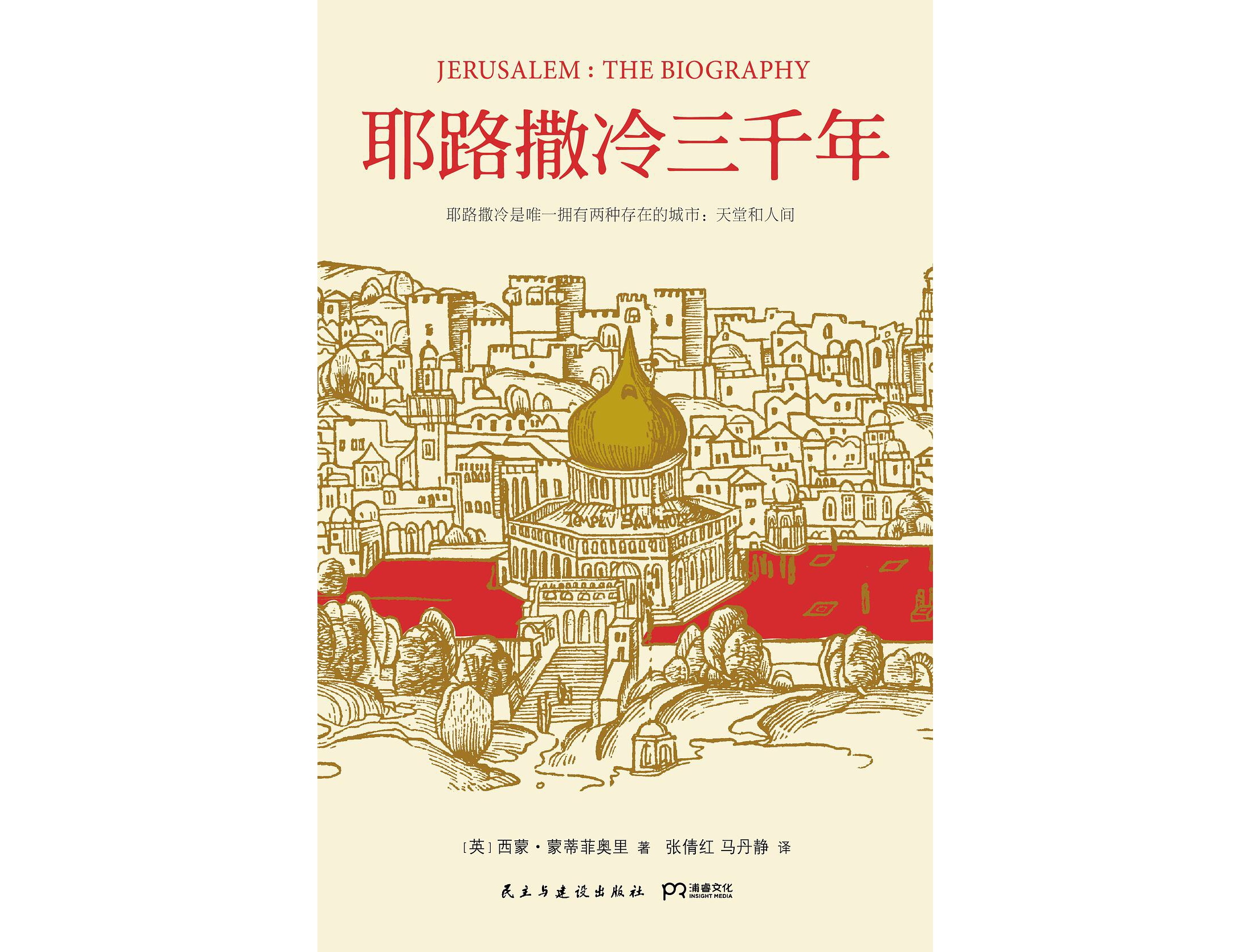
《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 [英] 西蒙·蒙蒂菲奧里,譯者: 張倩紅 / 馬丹靜,版本: 浦睿文化|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2015年1月
這段歷史錯綜複雜,即便相當熟悉它的人可能也會發現新奇之處。2007年,英國作家和歷史學家詹姆斯·巴爾(1976— )閱讀新近解密、此前從未公布過的英國軍情五處檔案時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細節:1945年初,軍情五處一名特工報告稱,正在巴勒斯坦地區搞暗殺、炸彈襲擊來對抗英國政府的猶太人恐怖組織的軍火和經費來自法國人的支援。此時二戰還沒有結束,英國和戴高樂領導下的自由法國是並肩作戰共同對抗希特勒的盟友,而戴高樂手下的人在秘密為反英武裝提供支援。這是巴爾的歷史著作《瓜分沙洲:英國、法國與塑造中東的鬥爭》的開頭。
如果說這令人瞠目結舌,那麼巴爾的新書《沙漠之王:英美爭奪中東主宰權的鬥爭》的開頭更是令人大跌眼鏡:20世紀40年代末,英國政治家、中東通以諾·鮑威爾(Enoch Powell)告訴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伊登(後來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的英國首相):「在中東,我們的頭號敵人是美國。」
這兩本比較新的歷史著作分別從英法關係和英美關係的角度敘述和分析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60年代的中東現代史,視角獨特。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中東問題方面西方世界內部的殘酷競爭和鬥爭,這是一般很少被提及的問題,因為至少在公眾眼裡,英美是堅定的盟友,英法也是一團和氣。
社科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品牌已推出《瓜分沙洲》中文版,即將推出《沙漠之王》。巴爾畢業於牛津大學,目前為倫敦國王學院訪問學者,還開設自己的政策諮詢公司。他主要關注中東現代史,除了上面兩本書之外,還著有《點燃沙漠:T.E.勞倫斯與英國在阿拉伯半島的秘密戰爭,1916—1918》。巴爾的兩本獨特的中東歷史著作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我有幸於2018年9月在倫敦採訪了巴爾。

英國作家和歷史學家詹姆斯·巴爾(1976— )。
在中東爭權奪利的英法殖民者
新京報:你如何開始對中東感興趣?
巴:我在牛津大學讀的是現代歷史,中東研究不是我的本業。
2001年我第一次去了以色列,對該地區發生了興趣,決心以後再來。後來發生了9·
11
事件。次年我去了敘利亞,對敘利亞也產生了濃厚興趣,後來就寫了一本阿拉伯的勞倫斯的傳記《點燃沙漠:T.E.勞倫斯與英國在阿拉伯半島的秘密戰爭,1916—1918》(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T. 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 Arabia, 1916-1918)。勞倫斯在中東範圍的英法關係里發揮了重要作用。我最感興趣的一點是,世人都知道勞倫斯是親阿拉伯的,他希望幫助阿拉伯人的獨立運動,但我們很少談到他的另一面:仇視法國。當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法是盟友,但矛盾和衝突不斷,好多次險些撕破臉皮,反法的英國人很多,勞倫斯只是其中一個。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T. 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 Arabia, 1916-1918, 作者: James Barr, 版本: W. W. Norton & Company, 2009年7月
我決定深入探討一下在中東問題上英法之間的惡劣關係,於是花了四五年時間寫了《瓜分沙洲》。在這期間我第二次去了敘利亞,重點看它的東部地區,以及黎巴嫩。為了寫作和研究,我還去了沙烏地阿拉伯和葉門。我追蹤了勞倫斯活動和戰鬥的足跡。檔案和史料工作很重要,但對於中東研究來講,親眼看到地理條件和風景同樣重要。今天在沙特旅行還是很困難。這種現象近期有所改變,沙特開始發放旅遊簽證,但對遊客的控制很嚴格,讓他們不能自由行動。
作為非穆斯林,我沒法去麥加,而在麥地那下了飛機之後,可以清楚看到非常大的標語「非穆斯林不得進入」等等。勞倫斯曾經作為基地的傑達古城只剩下一小部分,沒什麼可看的了。不過在沙漠里還能看到當年鐵路遭襲擊之後的遺迹,那是勞倫斯的游擊隊乾的。大約每隔十公里可以看見奧斯曼軍隊為了保護鐵路線而建造的碉堡的殘骸。沙特政府不喜歡承認一戰期間的阿拉伯大起義,因為那是哈希姆家族的故事,不是沙特家族的故事。結果《點燃沙漠》在沙特被禁了。
我在寫作《瓜分沙洲》期間在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的中東研究中心當訪問學者,和中心主任尤金·羅根很熟。他對我幫助很大。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中東研究者,精通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能夠使用這些語言的史料。他的《奧斯曼帝國的衰亡 : 一戰中東,1914—1920》非常棒,但我相信他的《阿拉伯人:一部歷史》更精彩。這樣一部涉及廣泛而高水準的通史,非常見功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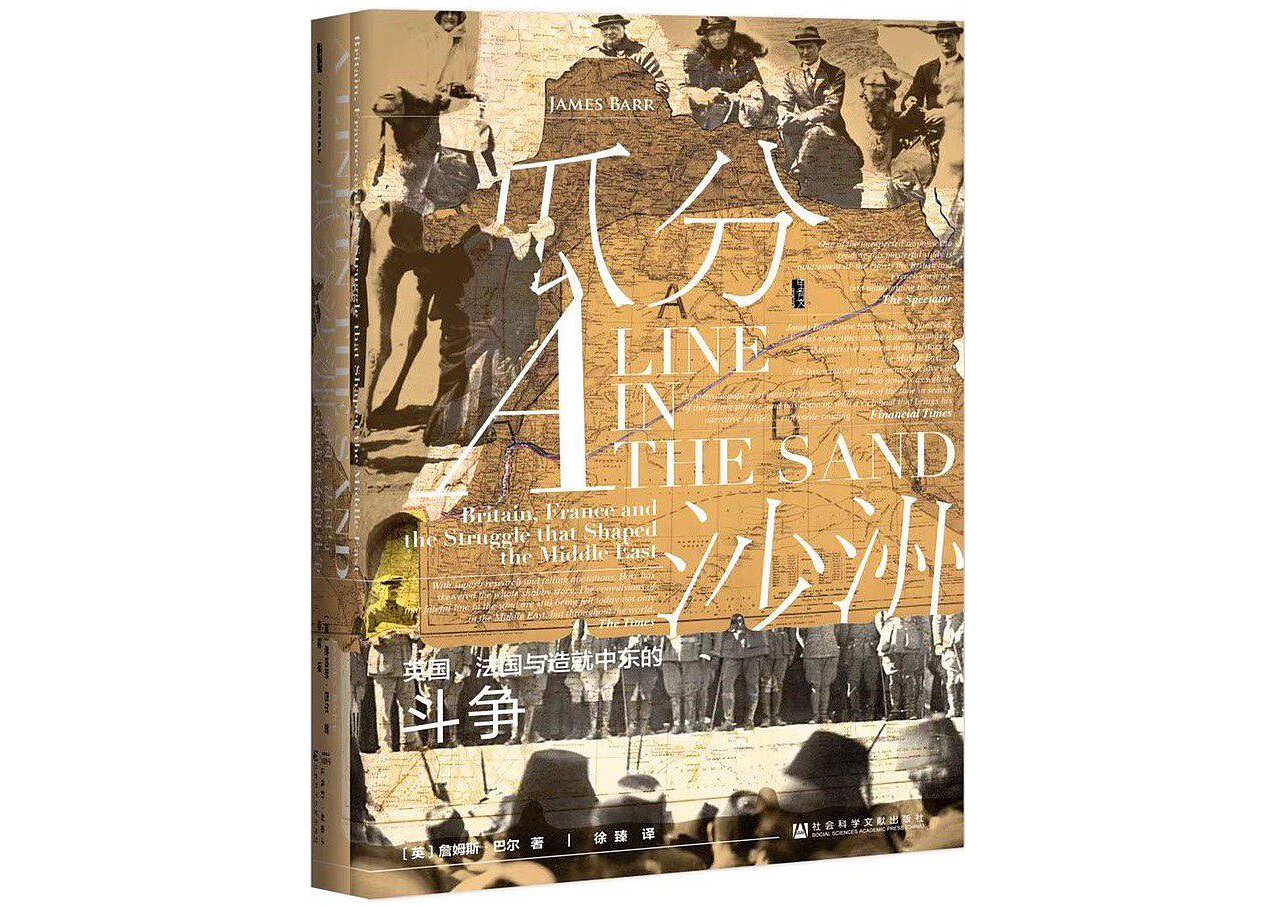
《瓜分沙洲:英國、法國與塑造中東的鬥爭》,作者:(英)詹姆斯·巴爾,譯者:徐臻,版本:2018年9月
新京報:我覺得《瓜分沙洲》這本書最有趣的一點就是深刻揭露了20世紀上半葉英法兩國在中東長期矛盾和鬥爭的很多不堪的細節,生動描繪了法國帝國主義的種種醜陋。法國讀者對這本書有意見嗎?
巴:《瓜分沙洲》的主題不是中東現代史,而是它的一個方面,即英法在中東的爭權奪利。
《瓜分沙洲》已經被翻譯為法文,2017年出版。法國讀者其實挺喜歡這本書,這讓我很驚訝,因為本書對法國在中東的殖民活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但法國讀者對我的「打臉」不介意,他們說畢竟歷史就是這個樣子。
我想,書里的有些細節對法國人來說也很新鮮。20世紀上半葉,英法兩國的人都很清楚,他們之間在中東開展了兇殘惡毒的競爭,互相拆台,互相使陰招,兩國之間充滿了敵意。法國殖民地的德魯茲教派武裝反抗法國的時候,英國人秘密為這些起義者提供武器和支援;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以恐怖主義對抗英國,企圖建立自己國家的時候,猶太人得到了法國政府的秘密支持和軍火供應。二戰前半期,在中東,英國最大的敵人是維希法國。戴高樂的自由法國和英國之間也衝突不斷。但後來隨著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推進,英國人和法國人都漸漸遺忘了這段奇怪的故事,彷彿英法一直是並肩抵抗法西斯的好戰友。
今天的法國公眾願意重新審視這段歷史,並且喜歡本書的一個證據就是,法國國防部資助了本書的翻譯出版,法國前國防部長和現任外交部長讓-伊夫·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還專門接見了我。
新京報:英國在歷史上與中東有緊密的聯繫,畢竟英國是老牌帝國主義國家。英國研究中東也有深厚的傳統,比如中國人熟知的英國中東學者有伯納德·劉易斯(Bernard Lewis)、阿爾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等。可否評價一下英國的中東研究傳統?
巴:美國也有很好的中東研究,但英國的中東研究傳統有更悠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當時的英國中東研究和殖民擴張、殖民統治是捆綁在一起的,英國人開始研究中東,起初純粹是因為地緣政治的緣故。英國人對中東的興趣,完全起源於英國的全球戰略利益。當然現在研究和政治分開了。胡拉尼可以說是這種舊傳統的最後一人,他是英國政府官員,親身見證和參與過英帝國在中東統治的末期。
再舉個例子,我太太是醫生,專業是熱帶病醫學。英國人之所以會研究熱帶病,也和曾經的大英帝國有關聯。
伊斯蘭,是非常多元化的
新京報:在你的學習和研究過程中,哪些學者對你的影響最大?
巴:對我影響最大的一位學者,也和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有關係。那就是瑪格麗特·麥克米倫教授。她關於巴黎和會的名著《締造和平:1919巴黎和會及其開啟的戰後世界》非常精彩,文筆優美,而且非常詳細。我喜歡充滿有趣細節的書。巴黎和會是非常複雜的話題,她寫得井井有條,非常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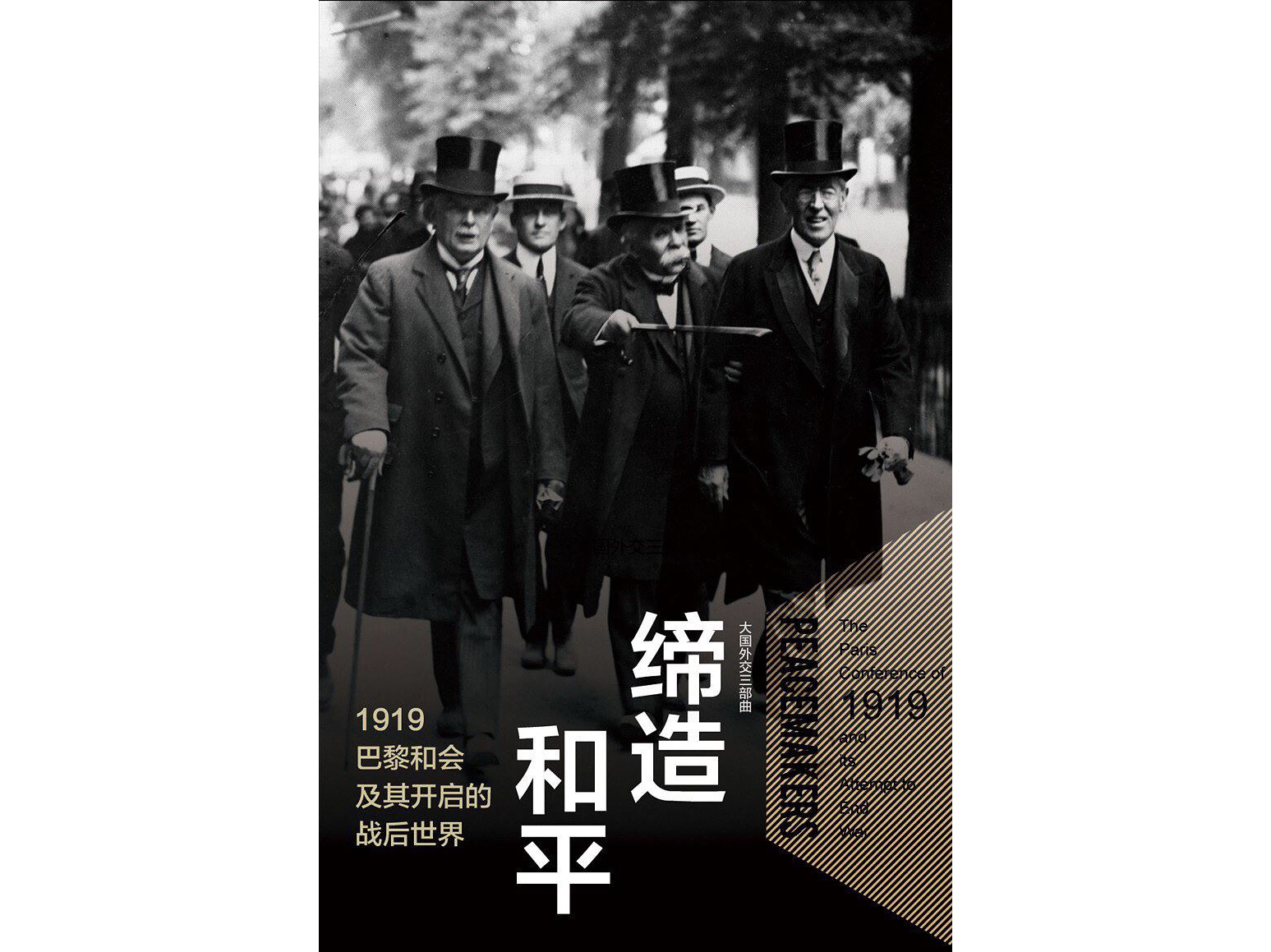
《締造和平:1919巴黎和會及其開啟的戰後世界》,作者:(加)瑪格麗特.麥克米倫,譯者:鄧峰,版本:2018年3月
新京報:《瓜分沙洲》寫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法在中東互相拆台,《沙漠之王》寫二戰之後英美在中東互相拆台,那麼你對另一個西方國家德國的中東角色有關注嗎?
巴:我還沒有關注過德國在中東的作用。不過關於這個話題,已經有一些不錯的書,比如斯科特·安德森的《阿拉伯的勞倫斯:戰爭、謊言、帝國愚行與現代中東的形成》,他以德國間諜庫爾特·普呂弗為線索,探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在中東的影響。
還有一本值得推薦的學術書是美國學者唐納德·麥克凱爾(Donald McKale)的《以革命為戰爭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與德國在中東》(War by Revolution: Germany and Great Britain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Era of World War I),詳細敘述和討論了德國如何試圖在中東煽動反對英法的伊斯蘭起義。
當然對於中東來說,我們把時間從一戰再往前推到19世紀末,德國對中東也產生了很大影響,主要在於新崛起的德國與老牌殖民帝國英法之間的鬥爭和緊張關係。我目前在考慮的下一本書可能會寫這方面。
新京報:你寫過勞倫斯的傳記《點燃沙漠》。另一位勞倫斯傳記家斯科特·安德森說 :「勞倫斯之所以能夠成為『阿拉伯的勞倫斯』,是因為沒有人關注他所在的戰場。」你是否同意?
巴:他說得完全正確。因為在一戰期間,英國人的固有思維是,打贏戰爭的場所必然是歐洲,是法國,因為那裡距離英國本土太近了。這麼想也不是沒有道理。而勞倫斯計劃所需的資源,相對於英國在西線的投入來說,是很少的,上級願意拿這麼少的本錢去賭一賭。他活動的自由空間也比較大。而一旦他開始取得成功,上級就更願意支持他,因為他的需求本身就不多。我在《瓜分沙洲》的美國版里計算過,勞倫斯的整個阿拉伯起義的經濟成本,也就是說英國對其的經濟投入,僅相當於西線戰場6到8個小時的開銷。
勞倫斯最初之所以被派去阿拉伯半島,是因為他的上級,吉爾伯特·克萊頓(英國駐開羅軍事情報單位的指揮官)非常信任他。當時克萊頓面對一個問題:很多人主張英國直接出兵,直接干預阿拉伯半島。他知道這樣做會導致災難,也不可能得到上級的批准、獲得足夠兵力去阿拉伯半島。所以在勞倫斯這趟出差還沒回來的時候,克萊頓就已經知道他的報告會怎麼寫:英國不能直接出兵,而應當用金錢和軍火來支持阿拉伯人的起義。
安德森的書以美國人威廉·耶魯和勞倫斯在戰前的邂逅開始,這種寫法非常聰明。但耶魯後來並沒有發揮重要作用,庫爾特·普呂弗的故事和勞倫斯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安德森的書寫得確實太棒了。
不過,有一點我不同意安德森。他用勞倫斯的回憶錄《智慧的七柱》為根據,說勞倫斯當時是這樣或那樣想的。問題是,勞倫斯把《智慧的七柱》重寫(或者說大幅度修改)了至少一次,甚至更多次,所以我們最終讀到的《智慧的七柱》里的觀點,是勞倫斯在戰爭結束很久以後的觀點。而如果我們讀勞倫斯的戰時日記、書信等,就會發現他在戰時的觀點和《智慧的七柱》略有不同。勞倫斯在戰後經歷了英國政府的背叛(或者說辜負),大失所望,所以他變成一個堅定反對帝國主義的人。安德森說勞倫斯一直是這樣的人。但我們讀勞倫斯的戰時文件會發現,雖然他對自己做的事情有懷疑(和其他很多英國人一樣),但他在很多時候仍然是帝國主義的走卒。
新京報:你如何評價勞倫斯這個人?
巴:很多人歌頌他,很多人惡評他,我大概站在中間位置。他肯定不是個容易相處的人。不過,很多人說他是撒謊成性、為自己塗脂抹粉的偽君子,我不能接受這種詆毀。他對歷史真相的確有一些改寫和操縱,比如出於反法的立場,他可能誇大了法國人對英國的惡意。他寫了名著《智慧的七柱》,所以讀者可能會覺得中東所有的大事都是圍繞他發展的,因為這本書實在深入人心。不過如果是別人寫書的話,對他的重要性的評價可能就沒有那麼高。所以說,筆的力量非常強大,勞倫斯很懂這一點。在戰爭末期他曾說「我們必須把報界爭取到我們這邊來」。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我前幾天才從史料里發現的。對於戰爭末期大馬士革形勢的第一份報道就是他寫的,登在英國陸軍的一份報紙上,後來《泰晤士報》轉發了這篇報道,而沒有說原作者是誰。他是個非常精明的宣傳工作者。
但是,如果沒有他的話,阿拉伯起義不可能成功。因為是他說服英國高層向該地區投入資源。
新京報:
1
914年末奧斯曼帝國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蘇丹以哈里發的身份號召全體穆斯林開展針對英法的聖戰。英國人對此十分緊張和擔憂,因為它的兩個重要殖民地埃及、印度都有大量穆斯林。德國人也企圖利用這一點,向阿拉伯世界示好,希望阿拉伯人起來反抗英法,從而減輕德國在歐洲的壓力。但事實證明,奧斯曼帝國的穆斯林臣民,以及英國統治下的中東、北非和南亞的穆斯林並沒有像蘇丹和德國人希望的那樣,紛紛揭竿而起反抗英國統治。這是為什麼?哈里發的呼籲為什麼沒有效力?
巴:我覺得,伊斯蘭是非常多元化的,有很多不同的潮流和運動。當時的奧斯曼蘇丹作為名義上的哈里發,早已經不能代表整個伊斯蘭世界。一戰期間,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內發生了一些反英暴動。蘇丹的呼籲發出之後,至少在英國人眼裡,這樣的反英暴動是對蘇丹的響應。英國人高估了蘇丹的號召力。
不過,英國人的擔心不是空穴來風。確實有一些煽動的書信從伊斯坦布爾被送到埃及和印度,即大英帝國的兩個最重要的殖民地,同時也是擁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領地。穆斯林世界大範圍響應蘇丹號召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假如發生就會產生很大的衝擊,英國就不得不從西線調走大量兵力和資源。英國人不掉以輕心是對的。
西方人在中東大多是扮演陰險歹毒的角色?
新京報:我們把法國和英國治理殖民地的手段做個比較,法國似乎總是顯得更粗暴和殘忍。《瓜分沙洲》里多次寫到,阿拉伯人表示寧願要英國統治,而不要法國。英國人真的比法國人更仁慈,還是兩國的統治手段不同?
巴:法國努力去管理自己的中東殖民地,但法國管理殖民地的經驗不如英國,沒有英國那樣歷史悠久的殖民傳統和管理技能,殖民地管理方面的人才(公務員)也沒有英國那麼多。比如,在英國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很多英國公務員從20世紀20年代初就在那裡工作和生活,花了二十幾年時間,認真想把這片土地管理得井井有條,努力促成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和解。當然這些英國人始終沒有成功,最後不得不放棄努力。
法國缺少這樣專業、有責任心和願意在巴勒斯坦待上十幾年、二十幾年的公務員。有人說英國在巴勒斯坦實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故意挑唆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衝突,從而讓英國人有理由留下擔當「裁判」。這種說法貌似有一定道理,但我從來沒有讀到過能夠支撐這種觀點的史料。
但在法國的敘利亞和黎巴嫩殖民地方面,有明確的史料表明法國人有意識地實行分而治之的策略,刻意激化和升級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等群體之間的矛盾。比如在敘利亞,法國人把這片土地分割成若干個小國,如南部的德魯茲教派的小國、以大馬士革為中心的小國、以阿勒頗為中心的小國、沿海的阿拉維派小國。在敘利亞,基督教馬龍派、阿拉維派穆斯林、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等群體之間的差異和矛盾是在法國人到來之前就存在的,但在奧斯曼時代和之前,敘利亞的諸多民族和宗教群體能夠相對安寧地共存。敘利亞在古代以貿易聞名,貿易需要安寧和互相信任。一個顯著的例子是霍姆斯城,它的絲綢貿易在古代很有名。霍姆斯位於敘利亞的地理十字路口,表現出了多宗教匯聚的氣氛。當地的天際線上不僅有清真寺的宣禮塔,還有天主教教堂的尖塔與東正教教堂的穹頂。所以我說,在法國人到來之前,敘利亞的五花八門群體能夠相對和平地共存。
而法國人來了之後就刻意地突出這些群體之間的差異,鼓勵他們互相摩擦和衝突,從而方便法國人的統治。比如,法國人特意扶植阿拉維派這樣一個宗教少數派,阿薩德家族就是這個教派的。法國人在敘利亞建立的土著軍隊里,大部分士兵是遜尼派,而軍官除了法國人就是阿拉維派。結果一直到今天,阿拉維派都把持著敘利亞軍隊。
英國殖民者更願意與當地現有的政治和文化機構合作,願意變通。而法國殖民者的手段更為直接、僵化和粗暴。法國人更想將自己的辦事方式強加於殖民地。20年代在鎮壓敘利亞的各種起義時,法國人的確表現得很殘酷。但英國人在鎮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起義時同樣殘酷,不過英國人可能更擅長掩飾和操控輿論。比如在30年代,與阿拉伯土著衝突激烈的時候,英國人努力封鎖消息,阻止外國記者進入巴勒斯坦。而20年代法國人在敘利亞鎮壓阿拉伯人的時候,英國人就派記者去敘利亞,報道法國人的暴行,拆法國人的台。英國人知道,如果國際社會的注意力集中到法國人的暴行上,就會不那麼注意英國人在巴勒斯坦的所作所為。
新京報:你的兩本書里,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在中東扮演的大多是陰險歹毒的角色。有沒有什麼人物是你欽佩的?
巴:即便那些陰險之徒,有一些其實是值得欽佩的。我很佩服愛德華·斯皮爾斯(Edward Louis Spears,1886—1974),儘管他不討人喜歡,但他是個非常有意思的歷史人物。他是丘吉爾的好友,也是最早主張支持戴高樂的英國人之一,並幫助戴高樂逃到英國。但後來在中東利益等問題上,他又成為戴高樂的死敵。

愛德華·斯皮爾斯(Edward Louis Spears,1886—1974),1942年。
美國政治家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1892—1944)也是個精彩人物,他堅決反對殖民主義的立場在當時是很進步的。他曾代表共和黨在1940年參加美國總統大選,與富蘭克林·羅斯福競爭,最後失敗。1944年美國大選期間他沒有得到本黨的提名,後來去世了。如果他能活下去,我相信他有可能成為美國總統,並且是一位優秀的總統。值得注意的是,羅斯福起初把威爾基當作潛在的競爭對手和威脅,後來又扶植和幫助他,培養他成為自己的接班人。
戴高樂是我欽佩的另一個歷史人物。他摸到手的牌極差,能夠使用的資源極少,但他把自己手裡的臭牌打得極好。這非常能體現水平。當然,他也不是一個容易相處的人。
新京報:中東經歷了英法爭霸、英美爭霸和美蘇爭霸,如今美國仍然在強有力地參與中東事務,近幾年俄羅斯也開始干預中東。這給我的印象是,阿拉伯人始終是別人的遊戲里的棋子。這種歷史教訓對今天有什麼助益嗎?
巴:阿拉伯人並非始終是消極被動、任人擺布的棋子。他們有主動性和自主意識。他們也懂得英法、英美和美蘇在玩什麼遊戲,所以會努力利用這些霸權之間的矛盾,為自己儘可能爭


※《摘金奇緣》亞裔只是包裝,仍是好萊塢老配方
※頸間暖意 圍巾邂逅降溫季
TAG:新京報 |
